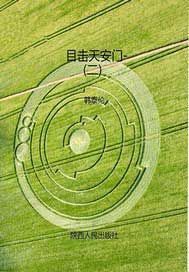第37章 克林顿访华谱新曲!江泽民迎宾开纪元(8)
说到历史,克林顿肯定知道这一悲剧的倒霉的始作俑者,两百多年前奉英王之命前来中国觐见乾隆皇帝的英国特使:马葛尔尼(又译马噶尔尼)。他怀着地球上两个大国彼此通商共同繁荣的梦想,率领着一支满载礼品(当然,清廷只把它们称为贡品)的船队,远涉重洋来到中国。但他做梦也没有想到,阻止他完成使命的障碍,既不是通商上的利益之争,也非礼品的不够庄重,而是一个简单而又关乎荣誉的问题:叩头。他如果想获得皇帝的召见,必须按照大清朝的规矩行三跪九叩之礼。
对于马葛尔尼来说,下跪叩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即使对自己的国君英王乔治三世,他也从不叩头。不要说九次,一次也不会叩,只能行单膝下跪礼。在他的一生里,他只对上帝双膝下跪。于是经过两天的思考,他郑重地向清廷申明,他绝不会对别国君王行高过自己国君的礼仪,即使冒被处死的危险。对此,乾隆的答复极为简单:“朕意深为不惬。”
表面看,这是一次双方缺乏了解的礼仪危机。然而实际上,几乎所有后来的历史学家都得出结论,危机的背后包含着更为复杂的文化原因。在乾隆看来,大清帝国作为世界的中心,接见一个来自蛮夷之邦的使节,已经是恩泽如山的举动。而英国人居然对天朝世代沿袭的礼节提出异议,正是“夷性贪得便宜,待之愈厚,则其心益骄”的表现。而对马葛尔尼来说,他是在捍卫英国的荣誉,捍卫自己国家赖以存在的价值――个人尊严、国家平等和自由交易的原则。尽管乾隆几乎相信了朝廷重臣和王申企图缓解冲突的蒙骗之词:番夷的身体构造与天朝子民不同,他们因为没有膝盖骨而无法下跪,但还是感到怒不可遏。一个古老国家自古以来的礼仪,竟然要被一个蛮夷之邦的使节违背。
不屑说,英国使团的来访最终以失败而告终。皇帝没有像英国特使所期望的那样,在北京的金銮殿接见他,而是借着在热河给自己祝寿的机会,让马葛尔尼庞大的使团又多跋涉了几百里地,然后混在各国祝寿使节的队列里顺带接见了一下。当然,皇上并没觉得这是一种惩罚,没有把这些傲慢的英吉利番夷不加接见就打发回去,已经算是皇恩浩荡了。因此,老皇帝决定不给英国任何通商的权利,甚至对英国使团带来的几船代表了当时先进科技的礼品(贡品?)也充满蔑视,其中包括一次可以连射八发子弹的马枪和天文地理音乐钟。“天朝物产丰富,无所不有”,英国人的“贡品”只不过是些“奇技淫巧”而已。遗憾的是,后来的历史极为残酷地纠正了乾隆的这一判断,正是这些“奇技淫巧”,有一天变成了火炮和铁甲快船,在四十多年后用战争敲开了天朝的大门。
此后的70年里,天朝从天上掉到了冷酷的人间,几千年建立起来的伦常道统,几百年锻造出的大清秩序,被一点一点地蚕食和瓦解了。大清朝无数次徒劳地试图把门再关上,西方列强又一次一次持枪破门而入。这期间的每一个皇帝以及专权近五十年的慈禧太后,都在迷惑不解地追问:我们自己过得好好的,这些洋人为什么总跟我们过不去呢?
于是一大堆迫使清廷开放门户的条约签订了。既然签了条约,那就按照条约规定做生意吧。不,这是一些强加给大清国的条约,是不平等的条约,必须一有机会就加以抵制。然而对于洋人来说,条约正好消除了力量上的不平等,用一种互相可以接受的常态来替代武力的肆虐。它制止了双方力量悬殊的战争带来的破坏性,回复到和平的逻辑上处理国家之间的事物。但在中国人看来,这是多么地不平等。不过且慢,中华帝国过去同别人讲过平等吗?“大皇帝君临万国,恩被四表,无论内地外夷,均系大皇帝百姓。”因此,中国与任何蛮夷属国之间的不平等,是天经地义的事情。现在,竟然有人把“平等”强加给了天朝,让命定的未开化的附庸同上天指定的帝王平起平坐,这是多么令人难以忍受的事情啊!太不平等了!
这一巨大的变故,打破了中国人一成不变的生活规矩,搅乱了中国人淡泊宁静的思想。它把理性强加给了中国人,迫使他们放弃固守了两千年的儒家道统,毫不留情地戳穿了中国人的幻觉。那时,有谁能预言这种做法会给中国带来什么样的后遗症呢?显然,中国人在灵魂深处受到了难以治愈的伤害,这种情形就像有人想用拳头告诉一个性情孤僻的孩子,世界上并不只有他一个人。这一伤害,历经百年而不愈,只要经人稍加煽动,立刻转变为取之不尽的民族仇恨和反抗外来者的精神资源。这一可怕的力量,在中国现代历史的进程中,一次次轻而易举地击溃了任何想按照西方模式进行现代化改造的企图。仿佛一道符咒,中国人只有通过起义、暴动、仇外和内战,才能平复这一深深的创伤。
西方人呢?在1949年以前一直继续按照他们的理性与中国打交道,然后一直继续与这个古老的大国发生冲突。他们也在不停地问:这样一个幅员广大、有着辉煌的文化历史、尊贵骄傲的国家,为什么就不能顺应世界潮流,与其他民族携起手来,共同创造这个世界的辉煌,同时也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呢?他们的顽固不化和不可理喻的根源到底来自哪里?怎样才能改变?
中国在鸦片战争以后的半个多世纪里仿佛走进了怪圈。由于“条约”是不平等的,因此一有机会就应该推翻。另一方呢,由于坚信国家间的契约如法律般不可动摇,一经违反便必须由武力来恢复。于是战争联绵不断,于是条约也签订得越来越多,西方对中国的瓜分也越来越深入。然后再被中国推翻,然后再次带来战争。就这样周而复始,一个古老骄傲的帝国,在自己家里持续不断地上演着被外族掠夺的悲剧。
许多年过去了,事情果真如这道符咒所预示的那样。尽管中国经历了天翻地覆的变故和创痛,但今天我们回头来看,情况似乎并没有太大的改变。如果仔细研究一下中国与西方交往的历史,东西方之间的误解和冲突,似乎仍旧沿着曾经发生过的悲剧模式继续重演。除了少数几个文人和知识分子,似乎没有人渴望真正的变革。中国的一切前进,似乎都是极不情愿地被外来力量推动的,或是暴力革命的副产品。只要不是迫不得已,中国总是希望把门再关起来,然后沉浸在天下第一大国的幻觉之中,沾沾自喜地过与世隔绝的生活。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和民族价值塑造的思想观念呢?中国无疑是人类历史上最大、持续时间最久的帝国,它的领土在乾隆统治时期达到顶峰,覆盖了从里海到琉球群岛、从贝加尔湖到暹罗湾之间的广大地区。这辽阔的领土被沙漠、大海、万里长城、精神偏见和认为帝国是“天下唯一的文明”的坚定信念保护着。这片领土之外的人民则是一些粗野的蛮夷(当他们因为“向往”天朝的文明而来顶礼膜拜时除外),他们的精神尚未开化,思想充满邪恶,他们之中如果有人来到中国,一定都是包藏祸心之辈,应该处处提防他们。另一方面,所有没奉皇上旨意离国的中国人,都应该永远不再回来,因为作为天朝的子民,脱离了皇上的荫蔽便无异于叛国。
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呢?他们认为自己的文化是最优越的,因为它代表了进步和现代性,也就是说,这一文化建立在科学、思想文化的交流和自由贸易的基础之上。他们相信,未来的世界一定是一个全球范围的贸易和交流的社会,只有最能适应这一社会的国家,才有可能成为未来的主人,否则就会被文明抛弃。英国的做法,显然旨在否认中国文化的有效性,认为不能同时存在几种文明。英国的做法像中国人一样具有排他性。世上只有一种文明,即西方文明,一切人类都要向这种文明进化。英国既是这一文明的代表,也是推动它在全球实现的动力。
于是,英国忙于驰骋在各个大洋之间,而中国则用墙把自己围住。英国鼓励个人自由和实现天赋权利,中国维持严格的等级制度并强调集体利益。英国不断革新和发现,中国满足于辉煌的历史。英国推崇自由往来,中国希望与世隔绝。总之,西方在不断创造一个开放的社会,中国则继续维持一个封闭的社会。正是这一价值观上的冲突,导致了中国同西方国家之间无穷无尽的争端。
同整个西方世界如此,同美国的关系又如何呢?
在鸦片战争之后的一百多年时间里,中国和美国之间的恩恩怨怨,几乎成了国际关系领域里一道最为复杂的风景。无论中国还是美国,一谈起对方,都无法简单地用一种说法概括。双方相互充满矛盾的感情,就像一对彼此既有好感又争吵不休的冤家。
从好的方面讲,美国没有像其他西方列强一样侵占过中国的领土,而且反对(至少在口头上)西方国家对中国的侵略。“华盛顿对几乎所有外国对中国的侵略都提出了抗议。”美国也是第一个退回部分庚子赔款的国家,并且督促清廷用这笔钱建立了中国第一所大学: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的前身)。美国的传教士在漫长的几百年时间里,除了隐忍和平地对中国人宣讲上帝的福音以外,还在中国开展了一系列行医和兴办教育的事业,为中国发展现代教育和西方医学做出了很多贡献。这些传教士还翻译和介绍了大批西方科学技术书籍到中国,培养了许多中国科学家和政治家。这些人里最突出的一位,就是传教士丁韪良(威廉?亚历山大?马丁),他毕其一生,帮助中国建立现代教育,被清廷重用,官至二品,被任命为京师大学堂的第一任校长。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积极支持中国抗击日本的侵略,给予中国大量无偿的经济和军事援助。战后,美国不顾英国的反对,坚决主张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使中国最终成为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
但是,尽管有这些事实的存在,美国仍可以被看作是中国的宿敌。美国是继英国之后第二个从海上侵入中国的国家。鸦片战争后不久的1844年,美国就和清廷签订了《望厦条约》,确定了中美两国的不平等关系。之后的一百年间,美国取得了与其他西方列强差不多的一切单方面特权,还带头取得了多种新的特权。美国在华的势力和影响不断扩大,从中国榨取的财富也越来越多,并且不断强迫或诱使中国人服从美国的旨意。直到1949年,这些特权才被取消,但是,美国又率领其他西方国家一道抵制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与台湾结盟,发动朝鲜战争,实行经济封锁等等。一直到1972年,出于冷战的考虑,才决定与中国恢复关系,联手抗衡苏联。时至今日,美国还被一些人认为是对中国进行“和平演变”的策源地,海外敌对势力的大本营。
甚至像费正清这样权威的美国学者,也得出结论说,中国人对中美关系的看法与美国人的看法大相径庭。美国人觉得跟中国的关系富于冒险性,令人振奋,而且在精神和物质两方面都有收获。但中国人认为美国与中国的接触是强加的,是来自外部的侵略,这种侵略是一种对中国的干扰、污辱和破坏。尽管中国人表面上对美国非常客气,但内心里并没有如美国人那样,对美中友好抱同样的热情。美国的中国史专家韩德也指出,历史上中国的领导人从蒋介石到毛泽东,虽然政治立场完全不同,但都认为美国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没有本质区别,都是为了掠夺才来中国。
那么,美国人又是怎样看待中国人的呢?按一位美国学者的话说,美国人认为中国人既智慧勤奋值得尊敬,又愚昧落后难以理喻。认为中国人的气质是一种相互极为矛盾的混合,既有近乎永恒的稳定,又有没完没了的混乱;既有圣人般的智慧,又有强烈迷信色彩的无知和无法预料的极端;既有哲理般的平静,又有爆炸性的狂热。而美国人对中国人的感情,也是一种矛盾的混合物,同情和排斥、慈爱和恼怒、友善与敌对、以及爱和近于恨的恐惧。实际上,美国对中国的这一“爱恨交织”的情感,几乎可以在美国对所有中国问题的态度上体现出来。
即使在中美关系正常化以后,两国间的深刻矛盾依然存在。中国人总是希望美国能够先表示尊敬,给足面子,不要对中国的所作所为横加指责,然后再来谈友好合作;美国则认为中国既然一直在做危害美国利益的事情,如何能对中国表示尊敬?中国试图告诉美国,我做对自己有利的事情,或者解决我自己家里的纠纷,并不劳你来多管闲事;美国试图告诉中国,你一直支持那些和我不好对付的人跟我作对,或者邀我去你们家作客时随便打孩子,而你又明明知道我反对打孩子,我如何能跟你作朋友呢?中国说,我是一个活了几千年的老人,有着辉煌的青年和壮年时代。虽然现在我老了,但还是知道怎么料理自己的生活。你只是个乳臭未干的毛孩子,有什么权利来教训我?美国的反应自然是,尽管我尊敬你,但是因为你太老了,所以才变成了顽固不化的人,不能接受新鲜事物,也跟不上时代的发展,正好需要听听我这个世界上最强壮的年青人的意见。
总之,双方各执一理,互不相让。如果说两国是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之争,毋宁说是地位尊卑之争。而且正因为这一年龄差距,两个国家几乎少有的在各个方面极端不同。从人口角度讲,美国人口构成极为多样化,中国则相对单一;从文化角度讲,美国宏扬个人主义,中国崇尚集体精神;美国强调个人自由,中国坚持个人应当服从集体;美国人热爱流动,中国人强调扎根故土;美国人推崇实干,中国人推崇话语;美国人欣赏年青和激情,中国人尊敬年长和智慧;从政治制度讲,美国极端强调民主与自由,中国一直倾向集权与控制;美国强调条文法律,中国依靠道德自律;从经济角度讲,美国富有,中国贫穷;美国鼓励消费和投资,中国鼓励节俭和储蓄。对于如此不同的两个国家,双方的领袖在文化定位上如何把握,的确是一个严峻的挑战。
因此,当克林顿把访华的第一站放在西安时,他实际上明确地透露出一个信息,美国对中国的理解自克林顿始,进入了把尊敬和探究文化差异作为改善和发展中美关系的一个重要考虑的时代。这一举动极不寻常,等于在过去干涩单调的国际政治行为里融进了情感因素,使之成为交往的正式内容,而不仅仅是谈判之余的娱乐活动。尽管它的意义还没有引起专家们的足够重视,但这一举动对未来以至下个世纪中美关系的影响会非常深远。
首先,对于一个美国总统来说,如果不是经历过六七十年代的文化反叛和反越战运动,这样的文化宽容和对价值多元尊重无从谈起。老一辈的美国领导人很少能对中国文化有如此真诚的兴趣。他们至多把这些遗产当作古迹来看待,不会设法通过这些东西去把握当代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思维习惯,以及这些表象与传统的联系。这些传统类型的西方政治家,尽管可以学会熟练地使用筷子,热爱吃中国餐,甚至欣赏明式家具和传统水墨画,然而一旦到了谈判桌上,立刻就会忘掉他的对手的文化背景和传统烙印。但是,我们从克林顿的讲话里看到,他可以很自然地把中国人的行为方式和生活态度与他看到和感受到的文化历史联系起来,真诚地看待这些差异,同时坚持自己的观点和价值,认真地与对方寻求达成共识的途径,从而有效地把握住了机会。没有这种把握,很难想象克林顿能够如此成功地和江泽民通过辩论主持了一台史无前例的新闻发布会。
其次,西安之行充满象征意义。国事访问首站从文化古城开始,开外国领导人来中国访问行程安排的先河。尽管江泽民主席访美时也是先去的美国历史城市威廉斯堡,但以文化城市作为中美领袖互访的首站,则是美方先提出的构想。克林顿在上海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时告诉记者说,我想由一个代表中国的历史、中国的文化、中国人民的传统形象的地方开始。我这样做完全是出于个人原因,因为我认为,如果你了解一个人的历史,则对你了解这个人的现在和将来很有帮助。另外,我这样做还因为我知道美国人民希望如此。对我来说这次访问的一个重大目的是让美国人民更多地了解中国,让中国人民更多地了解美国。这就是我为什么首先到达西安的原因。
这种安排标志着,国家之间的关系已经不仅仅是一种政治关系了,如果没有文化上的理解和尊重,单凭权衡计算政治利益的得失,是无法充分实现互信的。没有互信,自然谈不到“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的建立。当然,马葛尔尼205年前所遭遇的苦境不会再次重演(永无?),但两手空空而归的国事访问,在今天的世界里仍时常发生。
第三,西安按国宾待遇为克林顿举行中国古代传统的入城仪式,等于接受了美国两百年文化代表的平等地位,表明中国真正放弃了乾隆皇帝二百年前与西方开始交往时确定的居高临下屈尊俯就的位置,平等看待一切民族的文化传承和精神思想的来源。
因此,当克林顿总统接过西安城门的钥匙,迈着庄重欣慰的步伐走进十二朝的帝国之都时,他实际上挽着美国只有二百年历史的年青文化,第一次郑重地与两千年的文明站在了一起。那一刻,他面对眼前这座古老城池,心中满怀敬意,同时,他荣耀地站在那里,代表着世界上最强大的民族,因而也对自己国家年青而富于生命力的文化感到骄傲。他一定会想,如果能把这份对他人的尊敬和对自己的骄傲完美地运用到今后几天的活动中,他一定能和这个伟大的国家一起,创造一个美好的未来。
第五节 北京:走开放大国之路(1)
几乎很少有记者预料到,江泽民与克林顿的公开记者会竟然成为了一次亦庄亦谐的讨论会。谈到达赖喇嘛和西藏问题时,江泽民同克林顿都表示出特别的轻松和风趣。一位记者请他谈一谈故宫观感,克林顿说:“精彩绝伦!”有七位北大学生对克林顿总统提问,内容涉及经济、中美关系、台湾问题等方面,有些问题极为尖锐,甚至具有挑衅的意味。克林顿表示,他对北京决定允许他在电视上和中国人民谈人权问题,感到很惊讶。
克林顿访问北京纪行
一、到访之前
北京通往八达岭长城的高速公路仅剩下一小段路面还没有铺通,人们正在加班加点工作。一位工人说,即将访问中国的美国总统克林顿有可能通过他亲手修建的公路登上长城。
没有人正式通知这位工人,克林顿总统要经由这条路去攀登长城,从一张别人扔掉的报纸上,这位筑路工人得知克林顿即将访问北京,于是他自己便做了这个大胆的猜测。
对于马葛尔尼来说,下跪叩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即使对自己的国君英王乔治三世,他也从不叩头。不要说九次,一次也不会叩,只能行单膝下跪礼。在他的一生里,他只对上帝双膝下跪。于是经过两天的思考,他郑重地向清廷申明,他绝不会对别国君王行高过自己国君的礼仪,即使冒被处死的危险。对此,乾隆的答复极为简单:“朕意深为不惬。”
表面看,这是一次双方缺乏了解的礼仪危机。然而实际上,几乎所有后来的历史学家都得出结论,危机的背后包含着更为复杂的文化原因。在乾隆看来,大清帝国作为世界的中心,接见一个来自蛮夷之邦的使节,已经是恩泽如山的举动。而英国人居然对天朝世代沿袭的礼节提出异议,正是“夷性贪得便宜,待之愈厚,则其心益骄”的表现。而对马葛尔尼来说,他是在捍卫英国的荣誉,捍卫自己国家赖以存在的价值――个人尊严、国家平等和自由交易的原则。尽管乾隆几乎相信了朝廷重臣和王申企图缓解冲突的蒙骗之词:番夷的身体构造与天朝子民不同,他们因为没有膝盖骨而无法下跪,但还是感到怒不可遏。一个古老国家自古以来的礼仪,竟然要被一个蛮夷之邦的使节违背。
不屑说,英国使团的来访最终以失败而告终。皇帝没有像英国特使所期望的那样,在北京的金銮殿接见他,而是借着在热河给自己祝寿的机会,让马葛尔尼庞大的使团又多跋涉了几百里地,然后混在各国祝寿使节的队列里顺带接见了一下。当然,皇上并没觉得这是一种惩罚,没有把这些傲慢的英吉利番夷不加接见就打发回去,已经算是皇恩浩荡了。因此,老皇帝决定不给英国任何通商的权利,甚至对英国使团带来的几船代表了当时先进科技的礼品(贡品?)也充满蔑视,其中包括一次可以连射八发子弹的马枪和天文地理音乐钟。“天朝物产丰富,无所不有”,英国人的“贡品”只不过是些“奇技淫巧”而已。遗憾的是,后来的历史极为残酷地纠正了乾隆的这一判断,正是这些“奇技淫巧”,有一天变成了火炮和铁甲快船,在四十多年后用战争敲开了天朝的大门。
此后的70年里,天朝从天上掉到了冷酷的人间,几千年建立起来的伦常道统,几百年锻造出的大清秩序,被一点一点地蚕食和瓦解了。大清朝无数次徒劳地试图把门再关上,西方列强又一次一次持枪破门而入。这期间的每一个皇帝以及专权近五十年的慈禧太后,都在迷惑不解地追问:我们自己过得好好的,这些洋人为什么总跟我们过不去呢?
于是一大堆迫使清廷开放门户的条约签订了。既然签了条约,那就按照条约规定做生意吧。不,这是一些强加给大清国的条约,是不平等的条约,必须一有机会就加以抵制。然而对于洋人来说,条约正好消除了力量上的不平等,用一种互相可以接受的常态来替代武力的肆虐。它制止了双方力量悬殊的战争带来的破坏性,回复到和平的逻辑上处理国家之间的事物。但在中国人看来,这是多么地不平等。不过且慢,中华帝国过去同别人讲过平等吗?“大皇帝君临万国,恩被四表,无论内地外夷,均系大皇帝百姓。”因此,中国与任何蛮夷属国之间的不平等,是天经地义的事情。现在,竟然有人把“平等”强加给了天朝,让命定的未开化的附庸同上天指定的帝王平起平坐,这是多么令人难以忍受的事情啊!太不平等了!
这一巨大的变故,打破了中国人一成不变的生活规矩,搅乱了中国人淡泊宁静的思想。它把理性强加给了中国人,迫使他们放弃固守了两千年的儒家道统,毫不留情地戳穿了中国人的幻觉。那时,有谁能预言这种做法会给中国带来什么样的后遗症呢?显然,中国人在灵魂深处受到了难以治愈的伤害,这种情形就像有人想用拳头告诉一个性情孤僻的孩子,世界上并不只有他一个人。这一伤害,历经百年而不愈,只要经人稍加煽动,立刻转变为取之不尽的民族仇恨和反抗外来者的精神资源。这一可怕的力量,在中国现代历史的进程中,一次次轻而易举地击溃了任何想按照西方模式进行现代化改造的企图。仿佛一道符咒,中国人只有通过起义、暴动、仇外和内战,才能平复这一深深的创伤。
西方人呢?在1949年以前一直继续按照他们的理性与中国打交道,然后一直继续与这个古老的大国发生冲突。他们也在不停地问:这样一个幅员广大、有着辉煌的文化历史、尊贵骄傲的国家,为什么就不能顺应世界潮流,与其他民族携起手来,共同创造这个世界的辉煌,同时也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呢?他们的顽固不化和不可理喻的根源到底来自哪里?怎样才能改变?
中国在鸦片战争以后的半个多世纪里仿佛走进了怪圈。由于“条约”是不平等的,因此一有机会就应该推翻。另一方呢,由于坚信国家间的契约如法律般不可动摇,一经违反便必须由武力来恢复。于是战争联绵不断,于是条约也签订得越来越多,西方对中国的瓜分也越来越深入。然后再被中国推翻,然后再次带来战争。就这样周而复始,一个古老骄傲的帝国,在自己家里持续不断地上演着被外族掠夺的悲剧。
许多年过去了,事情果真如这道符咒所预示的那样。尽管中国经历了天翻地覆的变故和创痛,但今天我们回头来看,情况似乎并没有太大的改变。如果仔细研究一下中国与西方交往的历史,东西方之间的误解和冲突,似乎仍旧沿着曾经发生过的悲剧模式继续重演。除了少数几个文人和知识分子,似乎没有人渴望真正的变革。中国的一切前进,似乎都是极不情愿地被外来力量推动的,或是暴力革命的副产品。只要不是迫不得已,中国总是希望把门再关起来,然后沉浸在天下第一大国的幻觉之中,沾沾自喜地过与世隔绝的生活。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和民族价值塑造的思想观念呢?中国无疑是人类历史上最大、持续时间最久的帝国,它的领土在乾隆统治时期达到顶峰,覆盖了从里海到琉球群岛、从贝加尔湖到暹罗湾之间的广大地区。这辽阔的领土被沙漠、大海、万里长城、精神偏见和认为帝国是“天下唯一的文明”的坚定信念保护着。这片领土之外的人民则是一些粗野的蛮夷(当他们因为“向往”天朝的文明而来顶礼膜拜时除外),他们的精神尚未开化,思想充满邪恶,他们之中如果有人来到中国,一定都是包藏祸心之辈,应该处处提防他们。另一方面,所有没奉皇上旨意离国的中国人,都应该永远不再回来,因为作为天朝的子民,脱离了皇上的荫蔽便无异于叛国。
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呢?他们认为自己的文化是最优越的,因为它代表了进步和现代性,也就是说,这一文化建立在科学、思想文化的交流和自由贸易的基础之上。他们相信,未来的世界一定是一个全球范围的贸易和交流的社会,只有最能适应这一社会的国家,才有可能成为未来的主人,否则就会被文明抛弃。英国的做法,显然旨在否认中国文化的有效性,认为不能同时存在几种文明。英国的做法像中国人一样具有排他性。世上只有一种文明,即西方文明,一切人类都要向这种文明进化。英国既是这一文明的代表,也是推动它在全球实现的动力。
于是,英国忙于驰骋在各个大洋之间,而中国则用墙把自己围住。英国鼓励个人自由和实现天赋权利,中国维持严格的等级制度并强调集体利益。英国不断革新和发现,中国满足于辉煌的历史。英国推崇自由往来,中国希望与世隔绝。总之,西方在不断创造一个开放的社会,中国则继续维持一个封闭的社会。正是这一价值观上的冲突,导致了中国同西方国家之间无穷无尽的争端。
同整个西方世界如此,同美国的关系又如何呢?
在鸦片战争之后的一百多年时间里,中国和美国之间的恩恩怨怨,几乎成了国际关系领域里一道最为复杂的风景。无论中国还是美国,一谈起对方,都无法简单地用一种说法概括。双方相互充满矛盾的感情,就像一对彼此既有好感又争吵不休的冤家。
从好的方面讲,美国没有像其他西方列强一样侵占过中国的领土,而且反对(至少在口头上)西方国家对中国的侵略。“华盛顿对几乎所有外国对中国的侵略都提出了抗议。”美国也是第一个退回部分庚子赔款的国家,并且督促清廷用这笔钱建立了中国第一所大学: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的前身)。美国的传教士在漫长的几百年时间里,除了隐忍和平地对中国人宣讲上帝的福音以外,还在中国开展了一系列行医和兴办教育的事业,为中国发展现代教育和西方医学做出了很多贡献。这些传教士还翻译和介绍了大批西方科学技术书籍到中国,培养了许多中国科学家和政治家。这些人里最突出的一位,就是传教士丁韪良(威廉?亚历山大?马丁),他毕其一生,帮助中国建立现代教育,被清廷重用,官至二品,被任命为京师大学堂的第一任校长。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积极支持中国抗击日本的侵略,给予中国大量无偿的经济和军事援助。战后,美国不顾英国的反对,坚决主张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使中国最终成为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
但是,尽管有这些事实的存在,美国仍可以被看作是中国的宿敌。美国是继英国之后第二个从海上侵入中国的国家。鸦片战争后不久的1844年,美国就和清廷签订了《望厦条约》,确定了中美两国的不平等关系。之后的一百年间,美国取得了与其他西方列强差不多的一切单方面特权,还带头取得了多种新的特权。美国在华的势力和影响不断扩大,从中国榨取的财富也越来越多,并且不断强迫或诱使中国人服从美国的旨意。直到1949年,这些特权才被取消,但是,美国又率领其他西方国家一道抵制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与台湾结盟,发动朝鲜战争,实行经济封锁等等。一直到1972年,出于冷战的考虑,才决定与中国恢复关系,联手抗衡苏联。时至今日,美国还被一些人认为是对中国进行“和平演变”的策源地,海外敌对势力的大本营。
甚至像费正清这样权威的美国学者,也得出结论说,中国人对中美关系的看法与美国人的看法大相径庭。美国人觉得跟中国的关系富于冒险性,令人振奋,而且在精神和物质两方面都有收获。但中国人认为美国与中国的接触是强加的,是来自外部的侵略,这种侵略是一种对中国的干扰、污辱和破坏。尽管中国人表面上对美国非常客气,但内心里并没有如美国人那样,对美中友好抱同样的热情。美国的中国史专家韩德也指出,历史上中国的领导人从蒋介石到毛泽东,虽然政治立场完全不同,但都认为美国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没有本质区别,都是为了掠夺才来中国。
那么,美国人又是怎样看待中国人的呢?按一位美国学者的话说,美国人认为中国人既智慧勤奋值得尊敬,又愚昧落后难以理喻。认为中国人的气质是一种相互极为矛盾的混合,既有近乎永恒的稳定,又有没完没了的混乱;既有圣人般的智慧,又有强烈迷信色彩的无知和无法预料的极端;既有哲理般的平静,又有爆炸性的狂热。而美国人对中国人的感情,也是一种矛盾的混合物,同情和排斥、慈爱和恼怒、友善与敌对、以及爱和近于恨的恐惧。实际上,美国对中国的这一“爱恨交织”的情感,几乎可以在美国对所有中国问题的态度上体现出来。
即使在中美关系正常化以后,两国间的深刻矛盾依然存在。中国人总是希望美国能够先表示尊敬,给足面子,不要对中国的所作所为横加指责,然后再来谈友好合作;美国则认为中国既然一直在做危害美国利益的事情,如何能对中国表示尊敬?中国试图告诉美国,我做对自己有利的事情,或者解决我自己家里的纠纷,并不劳你来多管闲事;美国试图告诉中国,你一直支持那些和我不好对付的人跟我作对,或者邀我去你们家作客时随便打孩子,而你又明明知道我反对打孩子,我如何能跟你作朋友呢?中国说,我是一个活了几千年的老人,有着辉煌的青年和壮年时代。虽然现在我老了,但还是知道怎么料理自己的生活。你只是个乳臭未干的毛孩子,有什么权利来教训我?美国的反应自然是,尽管我尊敬你,但是因为你太老了,所以才变成了顽固不化的人,不能接受新鲜事物,也跟不上时代的发展,正好需要听听我这个世界上最强壮的年青人的意见。
总之,双方各执一理,互不相让。如果说两国是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之争,毋宁说是地位尊卑之争。而且正因为这一年龄差距,两个国家几乎少有的在各个方面极端不同。从人口角度讲,美国人口构成极为多样化,中国则相对单一;从文化角度讲,美国宏扬个人主义,中国崇尚集体精神;美国强调个人自由,中国坚持个人应当服从集体;美国人热爱流动,中国人强调扎根故土;美国人推崇实干,中国人推崇话语;美国人欣赏年青和激情,中国人尊敬年长和智慧;从政治制度讲,美国极端强调民主与自由,中国一直倾向集权与控制;美国强调条文法律,中国依靠道德自律;从经济角度讲,美国富有,中国贫穷;美国鼓励消费和投资,中国鼓励节俭和储蓄。对于如此不同的两个国家,双方的领袖在文化定位上如何把握,的确是一个严峻的挑战。
因此,当克林顿把访华的第一站放在西安时,他实际上明确地透露出一个信息,美国对中国的理解自克林顿始,进入了把尊敬和探究文化差异作为改善和发展中美关系的一个重要考虑的时代。这一举动极不寻常,等于在过去干涩单调的国际政治行为里融进了情感因素,使之成为交往的正式内容,而不仅仅是谈判之余的娱乐活动。尽管它的意义还没有引起专家们的足够重视,但这一举动对未来以至下个世纪中美关系的影响会非常深远。
首先,对于一个美国总统来说,如果不是经历过六七十年代的文化反叛和反越战运动,这样的文化宽容和对价值多元尊重无从谈起。老一辈的美国领导人很少能对中国文化有如此真诚的兴趣。他们至多把这些遗产当作古迹来看待,不会设法通过这些东西去把握当代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思维习惯,以及这些表象与传统的联系。这些传统类型的西方政治家,尽管可以学会熟练地使用筷子,热爱吃中国餐,甚至欣赏明式家具和传统水墨画,然而一旦到了谈判桌上,立刻就会忘掉他的对手的文化背景和传统烙印。但是,我们从克林顿的讲话里看到,他可以很自然地把中国人的行为方式和生活态度与他看到和感受到的文化历史联系起来,真诚地看待这些差异,同时坚持自己的观点和价值,认真地与对方寻求达成共识的途径,从而有效地把握住了机会。没有这种把握,很难想象克林顿能够如此成功地和江泽民通过辩论主持了一台史无前例的新闻发布会。
其次,西安之行充满象征意义。国事访问首站从文化古城开始,开外国领导人来中国访问行程安排的先河。尽管江泽民主席访美时也是先去的美国历史城市威廉斯堡,但以文化城市作为中美领袖互访的首站,则是美方先提出的构想。克林顿在上海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时告诉记者说,我想由一个代表中国的历史、中国的文化、中国人民的传统形象的地方开始。我这样做完全是出于个人原因,因为我认为,如果你了解一个人的历史,则对你了解这个人的现在和将来很有帮助。另外,我这样做还因为我知道美国人民希望如此。对我来说这次访问的一个重大目的是让美国人民更多地了解中国,让中国人民更多地了解美国。这就是我为什么首先到达西安的原因。
这种安排标志着,国家之间的关系已经不仅仅是一种政治关系了,如果没有文化上的理解和尊重,单凭权衡计算政治利益的得失,是无法充分实现互信的。没有互信,自然谈不到“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的建立。当然,马葛尔尼205年前所遭遇的苦境不会再次重演(永无?),但两手空空而归的国事访问,在今天的世界里仍时常发生。
第三,西安按国宾待遇为克林顿举行中国古代传统的入城仪式,等于接受了美国两百年文化代表的平等地位,表明中国真正放弃了乾隆皇帝二百年前与西方开始交往时确定的居高临下屈尊俯就的位置,平等看待一切民族的文化传承和精神思想的来源。
因此,当克林顿总统接过西安城门的钥匙,迈着庄重欣慰的步伐走进十二朝的帝国之都时,他实际上挽着美国只有二百年历史的年青文化,第一次郑重地与两千年的文明站在了一起。那一刻,他面对眼前这座古老城池,心中满怀敬意,同时,他荣耀地站在那里,代表着世界上最强大的民族,因而也对自己国家年青而富于生命力的文化感到骄傲。他一定会想,如果能把这份对他人的尊敬和对自己的骄傲完美地运用到今后几天的活动中,他一定能和这个伟大的国家一起,创造一个美好的未来。
第五节 北京:走开放大国之路(1)
几乎很少有记者预料到,江泽民与克林顿的公开记者会竟然成为了一次亦庄亦谐的讨论会。谈到达赖喇嘛和西藏问题时,江泽民同克林顿都表示出特别的轻松和风趣。一位记者请他谈一谈故宫观感,克林顿说:“精彩绝伦!”有七位北大学生对克林顿总统提问,内容涉及经济、中美关系、台湾问题等方面,有些问题极为尖锐,甚至具有挑衅的意味。克林顿表示,他对北京决定允许他在电视上和中国人民谈人权问题,感到很惊讶。
克林顿访问北京纪行
一、到访之前
北京通往八达岭长城的高速公路仅剩下一小段路面还没有铺通,人们正在加班加点工作。一位工人说,即将访问中国的美国总统克林顿有可能通过他亲手修建的公路登上长城。
没有人正式通知这位工人,克林顿总统要经由这条路去攀登长城,从一张别人扔掉的报纸上,这位筑路工人得知克林顿即将访问北京,于是他自己便做了这个大胆的猜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