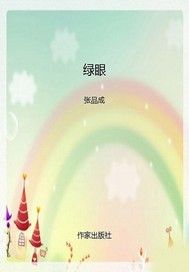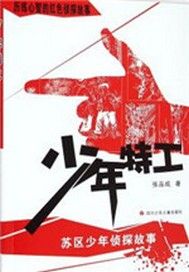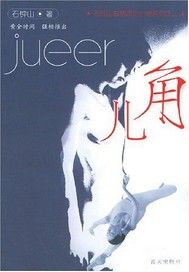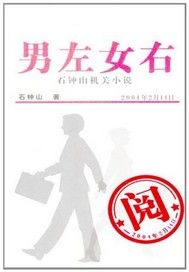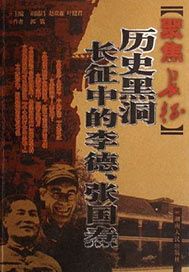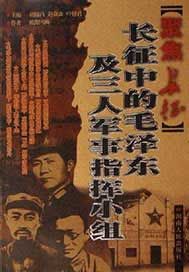第四十一章 论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及其阶级局限性
中国抗日战争,是在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进行的。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和第二次国共合作的特殊形式,抗日战争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两个战场,即由国民党军队担负的正面战场和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它们是相对独立的。但从抗日战争的总体上说,它们又是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是相互依存和相互配合的。过去在抗日战争的研究和教学工作中,一直未能对两个战场作统一的考察,对抗战初期的国民党战场虽然作过一些肯定,但就总体上说,对正面战场是否定的,往往是作为敌后战场的对立面出现的,有很大的片面性。这就无法科学地说明中国抗战这样一场全民族团结御侮的伟大的反侵略战争,也很难充分论证中国抗战在国际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伟大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列宁曾指出:“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研究历史的重要原则。因而我们要全面客观地分析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历史作用,既实事求是地评价它在抗战中的功绩,又实事求是地指出它的历史局限性,这样才有助于我们正确地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也有助于我们树立正确的历史观点。
一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开始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全面侵华战争。当时,中共中央通电全国,首先指明了这次事变的严重性质和坚决抗战的必要性。在日本灭亡中国方针的威胁下,在全国人民抗日浪潮的推动下,国民党开始改变过去的不抵抗政策,转而采取比较努力抗战的态度。
七七事变发生后,国民党政府虽然仍想通过外交谈判的途径力求避免“事态扩大”,但同时也对事变采取了比较强硬的立场。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提出解决卢沟桥事件的四个条件:(1)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之完整;(2)冀察行政组织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变;(3)中央所派地方官吏不能任人要求撤换;(4)第二十九军现在所驻地区不能受任何约束。谈话虽仍希望通过和平的外交方法解决,但表示中国已临到“最后关头”,“如果战端一开,就是地不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这个谈话的基本精神是好的,正式表明了中国政府的立场。这时日本已大量增兵关内,公开抛弃了所谓“不扩大方针”的欺骗宣传。7月30日相继占领北平、天津,8月13日又开始进攻上海。8月15日,日本正式成立以松井石根大将为司令官的上海派遣军,并下达了全国总动员令,于是开始了对中国的大规模战略进攻。
在这种情势下,中国政府采取了相应的措施。8月14日,中国政府发表《自卫抗战声明书》,宣告“中国决不放弃领土之任何部分,遇有侵略,惟有实行天赋之自卫权以应之”。15日,蒋介石下达总动员令,20日蒋自任陆海空军大元帅,决定将政府军事委员会作为战时最高统帅部,并将前线省份划为四个战区。与此同时,经中共中央一再呼吁和敦促,国民党对联共抗日也采取了积极态度。9月23日,蒋介石为中共关于国共合作宣言的公布发表谈话称在存亡危急之秋,更不应计较过去之一切,而当使全国国民彻底更始,力谋团结,以共保国家之生命与生存。使国共第二次合作得以实现,为实现全民族抗战创造了条件。
毛泽东曾指出:“国民党在1937年和1938年内,抗战是比较努力的,同我党的关系也比较好,对人民抗日运动虽有许多限制,但也允许有较多的自由”。这是符合历史实际的正确评价。在战略防御阶段,国民党及其军队的抗战是比较积极努力的,正面战场是有历史功绩的,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这个阶段,国民党正面战场是抗战的主要战场。
从一般军事学上说,在通常的情况下,正面战场总是担负着主要的作战任务。由于国民党实行的抗战路线和日军对华作战重点的变化,使国民党战场在抗战不同阶段所起的作用有很大的区别,但是,应当肯定,在抗战初期,国民党正面战场确是担负主要战场的作用。
从敌人方面看,这时日本凭借其兵力和军备上的优势,在战略上强调“速战速决”,企图集中兵力在最短时间内摧毁中国军队的抵抗能力,迫使中国政府屈服,实现其独占中国的目的。七七事变前后,日本军国主义者一再扬言三个月之内就可解决中国,当时的杉山陆相甚至叫嚣“支那事变可以在一个月内完全结束”。战争开始后,不断增加其侵华兵力,到1937年9月,日军侵华兵力已超过战争初期所预定的最高限额11个师团,达到了14个师团。它同时在华北和华东展开进攻,然后南下华中,幻想速战速决。到1938年1月16日日军占领南京后,日本政府发表声明(即第一次近卫声明):“帝国政府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谈判)对手,而期待真正能与帝国合作之中国新政权的建立与发展。”这些都说明,这时期日军作战是以国民党政府为主要对象,其目的是要摧垮国民党军事力量,迫使中国投降。
从国内方面看,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倡导者、组织者,对团结抗战的实现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有着良好的政治和军事素质。但在战争开始时,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只有几万人(当时在华北前线的八路军共32000人),武器装备很差,还不能给敌造成足够的威胁。而这时国民党是第一大党,处在执政地位,它参加抗战后,在一定程度上起了团结全国抗战力量的作用。1937年8月初,国民党政府在南京召开国防会议。中共代表朱德、周恩来、叶剑英应邀与会,共商国防问题。此外,广西、四川、云南、山西等地的地方首领白崇禧、刘湘、龙云、阎锡山等都参加了。原来国民党中央与地方实力派之间矛盾很深,互相猜疑,七七事变发生后,蒋介石曾电邀李宗仁、白崇禧到南京共商大计,龙云、刘湘曾电李、白劝阻,“未可轻易入京,万一抗日不成,反而失去自由”。可见疑虑之深。但在民族敌人生死威胁面前,使他们暂时捐弃前嫌,同意联合抗战。正如李宗仁所表示的:“今日的局势只有两条路可循,不是抗战图存,便是投降亡国。”表示要秉“先国难而后私仇”的大义,拥护中央参加抗战。因而这次作为抗战决策的南京国防会议,结束了国民党内部四分五裂,各自割据一方,内战迭起,纷争不已的局面。此后,各地军队陆续开赴前线作战。抗战初期,蒋介石先后调动近200万军队,在华北、华东和华中等地对日作战,他们除蒋介石的中央系统的张治中、朱绍良的第五集团军,陈诚、薛岳的第十五集团军,罗卓英的第十九集团军,卫立煌的第十四集团军,胡宗南的第十七军团,汤恩伯的第二十军团等外,还有许多地方实力派的部队,主要有:原东北军的于学忠五十一军,何柱国骑二军,廖澄流五十七军,刘多荃四十九军;原冯玉祥西北军旧部宋哲元的第一集团军,孙连仲的第二集团军,韩复榘(后为孙桐萱)的第三集团军;山西阎锡山部傅作义的第七集团军,商震的第二十集团军;广西李宗仁、白崇禧部李品仙的第十一集团军,夏威的第十六集团军,廖磊的第二十一集团军;四川刘湘的第二十三集团军,邓锡候的第二十二集团军,刘建绪的第十集团军,潘文华的第二十八集团军;广东余汉谋的第十二兵团,叶肇的六十六军,邓龙光的八十三军;云南龙云部卢汉的六十军,孙度的五十八军等等。这时开赴华北前线的八路军,以自己英勇顽强的战斗,积极配合了正面战场作战。当时《大公报》社评曾称:“中国此一战,征调兵队及于全国,凡奉命赴战的军队没有不勇敢,没有不拼命的。”总之,抗战初期国民党正面战场作为主要战场的作用是显见的。
第二,在这一阶段,国民党军比较积极认真地进行了正面防御作战,并打了一些硬仗。
抗战开始后,日军处战略进攻态势,中国处战略防御态势。南京国防会议根据敌强我弱的形势,确定实行“持久消耗战略”的国防方针,即以空间换取时间,以持久作战消耗敌人;同时根据日军主要以华北为进攻方向,因此决定在平汉、津浦两路沿线地区设置三道防线,以正面的阵地防御战来保守城市和战略要地。从全面抗战开始到武汉广州失守的十五个月战略防御阶段,国民党军队在华北、东南及华中两大战场开展正面防御作战,据统计,国民党军在这期间同日军进行重要战役战斗270多次,歼敌77万。其间著名的有忻口(太原)、淞沪、徐州、武汉等四次大的会战,并取得了台儿庄战役的胜利。
忻口(太原)会战,是华北战场上进行的一次较大规模的战役。
1937年7月30日,日军占领北平、天津后,即向华北纵深挺进。这时在华北战场上国民党军队约70万人。担负平汉线防守的为刘峙的第二集团军,担负津浦线防守的为宋哲元的第一集团军,担负平绥线防守的为汤恩伯的第十三军和高桂滋的第十七军。8月31日,日军正式编组以寿内寺一大将为司令官的华北方面军,辖八个师团,分兵三路沿平汉、平绥、津浦铁路线南下发动进攻。敌将主力置于平汉线方向,企图“迅速消灭河北省中部敌人”。国民党军队在保定、沧州一线节节抵御。由于守将刘峙畏敌退却,敌连陷固安、涿州后,9月24日占领保定,使原来准备在保定一线组织防御的计划未能实现。10月10日,敌攻陷华北重镇石家庄。随后,日军对平汉线取守势,将进攻重点转向山西,并以一部兵力进入正太铁路。而进攻平绥线的日军也于8月27日攻占军事重镇张家口,9月12日占领大同,敌坂桓第五师团则南下进入山西的浑源、灵丘一线,于是晋北告急。10月1日,日军部正式下达攻取太原的命令,并作出由晋北和晋东沿同蒲、正太两铁路线分进合击的部署,企图一举夺取山西,进而解决华北战局。
国民党政府曾提出“确保山西”的方针,当晋北告急时,阎锡山急令傅作义赶赴前线指挥,南京政府也急调卫立煌部由河北驰援晋北。中国部队部署平型关及内长城一线。总兵力六七万。这时奉命开赴山西作战的八路军一一五、一二〇师,到达雁门关、平型关一带,协同友军作战。9月25日,一一五师首战平型关,歼敌精锐坂垣师团一部千余人,取得华北抗战以来第一次胜利,极大地鼓舞了中国军民的抗战信心。敌在平型关受阻后,转而进攻平型关与雁门关之间的茹越口,中国守军经过激战后,于9月底全线后撤,山西内长城防线被突破。
10月初,为保卫太原,挽救危局,国民党第二战区先后集中十六个师十余万人,组成三个防御兵团,以卫立煌为前敌总指挥,在太原以北忻口地区组织会战,同时由孙连仲等部在太原娘子关一线阻敌西进,配合晋北主力决战。从10月13日起,敌5万余众向忻口阵地猛烈进攻,中国守军浴血奋战20多天,坚守住阵地。这时,八路军各部在敌后积极配合,五师、一二〇师频频出击,破坏交通,截断日军后方补给线,并一度占领雁门关,使敌弹药补给十分困难;10月19日,一二九师夜袭阳明堡,击毁敌机20余架,有力地配合了友军作战。忻口会战显示了中国军民抗战的威力,在近一个月的作战中,使敌无法前进一步,伤亡达3万多人。中国官兵牺牲也达10万之众,其中包括第九军军长郝梦龄、第五十四师师长刘家骐等。东线娘子关守军也进行了英勇抵抗,但因兵力分散,在强敌猛烈袭击下,10月26日娘子关陷落,守军全线撤退,敌进而逼近榆次、太原。娘子关失守后,忻口阵线动摇。11月2日,阎锡山下令忻口守军撤退。11月9日,太原失守。从此,华北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规防御战已基本结束,进入了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抗日游击战争阶段。
淞沪会战。这是正面战场进行的一次最艰苦激烈的会战。
当平津战事正激烈进行之际,日军又策动对上海的进攻,企图钳制中国军队主力,配合夺取华北,并进而占领沪宁,迅速迫使国民党政府屈服。八一三事变发生后,蒋介石即令在沪宁线驻守的张治中率两师兵力增援上海,痛击入侵之敌,同时任命冯玉祥为第三战区司令官,负担淞沪战场作战指挥(9月中旬以后蒋介石兼三战区司令官,顾祝同为副司令官,负责前线指挥)。国民党政府先后从各地调集到淞沪前线的军队达22个军50余师,总兵力为70万人。开始,日军以海陆军1万多人依靠海空优势火力的掩护,在上海北部地区登陆,向闸北等地进攻。由于兵力不足,在中国军队严重打击下,日军在狭小范围内无法展开,处于被动局面。8月底以后,日军由国内和台湾等地大量增兵上海,总兵力达30万人。双方战斗日趋激烈。敌我双方在宝山、罗店、大场、北站、浏河、吴淞、蕴藻浜、刘行、闸北、苏州河岸等地展开争夺战。战斗最激烈时,中国军队每小时伤亡达千人,主力各军都补充了四五次,下级军官伤亡达三分之二,旅团级军官伤亡也过半。日本大本营称,日军开始参战的两个师团(第三、第十一师团)人员已伤亡殆尽,全部以新的兵员补充,为日俄战争以来从未有过的损失。原来日军曾扬言十天即可占领上海,但却被中国军队拖住3个月之久。上海作战后期,由于日军大量增兵,而中国增援难继,已渐陷于被动地位,这时蒋介石为照顾所谓国际影响,仍一再下令坚守,致使前方损失惨重。11月初,日军在杭州湾金山卫和济河两翼登陆,迅速切断沪杭铁路线,9日攻陷松江,使中国军队腹背受敌,整个防御部署被打乱。为保存主力免遭围歼,蒋介石被迫下令全线撤退。11日,上海失陷。
此役,日军伤亡达6万人,中国军队伤亡近20万人。历时三月的淞沪抗战,有力地击破了日军“三月亡华”论,充分显示了中国军民抗战的力量。
日军占领上海后,随即沿沪宁铁路进攻南京。至12月初,敌已从东、南和西南三面进逼南京。国民党军队由于仓促组织防御,十几万部队又死守孤城,13日南京就被敌攻陷。日军在南京制造了亘古罕见的大惨案,30万和平居民惨遭屠杀。
台儿庄战役。这是徐州会战中的一个重要战役。
日军实现占领华北和宁、沪、杭后,遂将作战重点转向华中,企图首先夺取徐州,打通津浦路,使南北两个战场打成一片,然后集中力量攻取武汉。其时,沿津浦路南下的华北日军(第十师团)已占领济南,进抵兖州、济宁一线,敌第五师团则沿胶济铁路进犯,华北日军第十三师团也沿津浦线北犯,攻占了淮河北岸蚌埠等地。这时担任津浦路和徐州一线防御的是李宗仁为指挥的第五战区部队,加上增援的汤恩伯、孙连仲等部,总兵力达60万人。
1938年3月中旬,在敌第二军司令官西尾寿造指挥下,以第五师一部直趋临沂,第十师团向滕县等地进攻,企图会师后合攻台儿庄,消灭运河以北中国军队主力。进攻临沂之敌,受到守城庞炳勋部顽强抵抗,随后又得到增援的张自忠部配合,激战五昼夜,歼敌四千余,迫使日军退守莒县,从而粉碎了日军第五、十师团合攻台儿庄的计划。滕县守军在一二二师师长王铭章指挥下,与敌激战三昼夜,全部壮烈殉国。3月23日,敌第十师团开始进攻台儿庄。台儿庄位于徐州东北三十公里,扼运河的咽喉,具重要战略地位。李宗仁以一部兵力驻守台儿庄,正面牵制敌人,以主力置敌侧后,伺机歼敌。24日,敌以地面和空中猛烈炮火攻击台儿庄,中国守军奋勇作战,27日敌一部冲入台儿庄,双方展开巷战,反复争夺,战况惨烈,我守城部队伤亡过半。此时,在李宗仁的一再严令下,汤恩伯部由南向北从侧背攻击敌人,4月6日与守城部队发起反攻,内外夹击,大败日军,歼敌两万余人(毙敌七千余,击伤13000余人)。台儿庄战役是国民党正面战场取得的第一个较大的胜利,具有重要的意义。
日军在台儿庄受挫后,4月间即从华北及苏、皖等地调集重兵,合力围攻徐州。至5月初,敌十三个师团30余万兵力分六路进攻,形成了对徐州四面合围态势。为避免主力被歼,李宗仁决定全线撤退,跳出了敌包围圈。5月19日徐州失落。
徐州会战取得台儿庄战役的胜利,随后又保证了主力安全西撤,这从作战指导上说是比较正确的。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在徐州会战进行之际,国民党军副总参谋长白崇禧奉命去徐州协助李宗仁指挥作战,临行前,白曾专请周恩来商谈津浦战场的作战方针。周向他建议:津浦南段以运动作战为主,辅之以游击战,并已令新四军作战役配合,这样在广阔的淮河流域使日军时刻受到威胁,不敢贸然北上;在徐州以北则宜采取阵地战与运动战相结合的方针,守点打援,以达到各个击破的目的。后来在徐州会战中大致采纳了这个建议,在作战方法上比较积极主动,因而取得了成效。这是抗战初期国共合作的一段佳话。
武汉会战。6月15日,日本御前会议正式批准发动武汉战役,接着日军大本营又作出“以初秋为期,攻占武汉”的决定,其主要目的是占领国民党临时政治中心武汉,并配合夺取华南重地广州,进一步从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给中国以严重打击,迫使中国政府屈眼。敌先后集中了14个师团的兵力,以第十一军所属溯长江两岸西进为主攻方向,以第二军在淮河以南策应。国民党则在“保卫大武汉”的口号下,在武汉地区集结兵力100万人以上,以李宗仁的第五战区和陈诚的第九战区实施防御作战。
国民党军主力集中武汉外围沿长江两岸展开,战场遍及皖、赣、鄂、豫四省广大地区。武汉战役从1938年6月12日敌在安庆登陆开始,至8月下旬,主要是外围作战阶段,国民党军依托长江沿岸要塞和大别山麓地区进行了顽强抵抗。7月26日,敌占领九江,随后在长江方面越过了国民党军第一防御地带(鄱阳湖及大别山东麓一线)。8月下旬,日军大本营正式下达攻占武汉的作战命令,于是日军从南北两线分兵五路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国民党军节节抗击,阻敌前进。在武汉会战期间,国民党军同日军大小战斗数百次,并在南浔路、马头镇、富池口、大冶、半壁山、黄石港、田家镇、万家岭等地重创日军。至10月中旬,由于日军已突破国民党军第二防御地带(决战地带),对武汉形成了包围态势,在此情况下,国民党政府军委会于21目决定放弃武汉。25日,武汉失陷。
武汉战役历时四个多月,据国民党方面统计,敌伤亡达10万人以上,基本上达到了“作战四个月,予敌以最大之消耗”的目的,掩护了政府机构和经济文化设施的西迁,使日军速战速决的目的归于破产。
抗战初期国民党正面战场上述的四次大会战,基本上反映了这一时期国民党军队正面防御作战的情况。
第三,广大官兵作战勇敢,表现了中华儿女同仇敌忾,不怕牺牲的爱国精神。
抗战发动后,国民党军队官兵中长期被压抑的抗日爱国精神被激发起来了。同样一支军队,由于战争的目的性不同,会表现出完全相反的精神面貌。国民党军队在抗日战场上,除少数畏敌溃逃外,广大爱国官兵积极主动,浴血奋战,涌现了许多感人至深的英雄业绩。像在淞沪会战中,守卫宝山的姚子青营五百官兵,面对2000日军、30余艘敌舰,20多架飞机和近30辆坦克的攻击,奋勇抗击七昼夜,一次又一次打退敌人的进攻。最后日军施放硫磺弹,燃起全城熊熊烈火,敌军在战车掩护下冲入城内。全营官兵与敌巷战肉搏,激战两昼夜全部壮烈牺牲。当时沪《大美西报》曾著文赞叹此次姚营全部珣城,其伟大壮烈,实令人内心震动而肃然起敬,此非仅为中国人之光荣,亦为全人类之光荣。其伟绩将永垂史迹而不朽。又如,守军八十八师五二四团代团长谢晋元,奉命率五百多人从北站进驻四行仓库,掩护主力从苏州河北岸撤退。他受命后曾以诗明志,写道:“勇敢杀敌八百兵,抗敌豪情以诗鸣。谁怜爱国千行泪,说到倭奴气不平。”他们在人民群众的热情支援下,坚守阵地,奋战四昼夜,击退敌人六次进攻,歼敌200余人,击毁战车两辆,孤军伤亡37人。后奉命退入租界,被迫将武器交给租界当局,人被软禁在胶州公园。在三年多的孤军营生活中,谢晋元仍然励精图治,继续训练军队,准备重上战场杀敌。1941年4月24日,谢晋元惨遭叛徒谋害。国民党军队中的一些高级将领,也同样表现了可贵的民族气节和英勇杀敌的爱国精神。像第九军军长郝梦龄,过去曾参加过内战,痛感“流血千里,人民遭殃”,一度要求解甲归田。七七事变后,他主动请缨北上抗日,并与家人立下遗书,决心拼死在抗日疆场。忻口会战时,他任中央兵团指挥。在他寄出的最后一封家书中曾写道此次抗战乃民族国家生存之最后关头,抱定牺牲决心,不能成功即成仁,为争取最后胜利,使中华民族永存世界上,……故余牺牲亦有荣,为军人者,对国际战士,死可谓得其所矣。“在作战中,他身先士卒,终于履行了自己为国捐躯的誓言。此外,如佟麟阁、赵登禹、刘家麒、王铭章、李必蕃等将军,都先后以身殉国。毛泽东对他们的爱国牺牲精神曾给以很高的评价。赞誉为”崇高伟大的模范。
对于中国军队英勇顽强的抵抗,敌人也不能不感到震惊。如守卫台儿庄的池峰城师官兵,与攻入城内的敌人反复肉搏,血战经旬,在城寨被敌占领四分之三的险恶形势下,仍然死命支撑,最后夺回了失地。敌人目睹此壮烈场面,在战报中曾写道敌于狭窄的散兵壕内重叠相枕,力战而死之状,虽为敌人,睹其壮烈亦为之感叹。又说“尸山血海,非皇军所独有”。
总之,从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到1938年10月武汉、广州失陷期间国民党进行了比较顽强的抵抗并取得个别战役的胜利。但是,从整体上说,正面战场的防御作战是失败的,在仅仅十五个月的时间里,日军长驱直入,很快就囊括了华北、华中大片土地和华南的要地,历次会战也都以失败或退却告终。当然,对于这种情况,也应该给以全面的、客观的分析。
一方面,从根本上说,这是由敌强我弱的形势决定的。由于日本是采取战略进攻方针,中国居于战略防御地位,在战争的一定阶段上,敌能得到一定程度的胜利,我则将遭到一定程度的失败,这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我们在总体战略上,应自觉地采取战略的持久战。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应避免在不利条件下的无把握的决战,勇于实行必要的退却,虽然丧失若干土地,但赢得争取胜利的时间。“这是抗日战争的上策”。从这一方面看,抗战初期正面战场的防御作战是有历史意义的。其一,它打击了敌人的气焰,振奋了民族精神,从而比较顺利地实现了全国性的抗日高潮。战争初期,日本帝国主义曾大肆宣传中国“不堪一击”,幻想三个月就可以灭亡中国。但是,战端一开,中国不仅没有迅速地灭亡或屈服,相反却加强了抗战到底的民族意志,使日军速战速决的计划彻底破产。在这一时期,国民党不但调集了自己的200万军队参加抗战,成为防御作战的主要力量,而且在政治上也进行了一些有限度的改革,承认了中共及其他抗日党派的合法地位,修改了一些反动法令,公布了《抗战建国纲领》,成立了咨询性的国民参政佘等等。国民党作为一个执政的党,在军事上和政治上采取了这些抗战的措施,是有利于统一全国抗战的力量。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时期的国民党政府是起了国防政府的作用。毛泽东曾指出:“抗战以来,把国内各个互相对立的阶级、党派、集团都团结起来了,各个不同的区域,不同的军队,都统一于国民政府与军事委员会指挥之下了,抗战十五个月的坚持,没有这个统一团结是不可能的。”正因为这样,使抗战初期比较顺利地出现了全国军民抗日的高潮和蓬勃向上的新气象。其二,争取了十五个月时间,为实现持久抗战创造了条件。这一时期虽然丧失了大片国土,但也给敌人在军事上和经济上造成了严重困难,迫使它不得不停止战略性的进攻。这就使我赢得了时间,保障了我国政治机构和军队主力逐渐西移,也使一部分经济和文化设施能够由沿海迁往内地,从而有可能在大西南和西北建立新的战略基地,使持久抗战得以实现。同时应该指出,国民党军队的正面防御,在客观上也掩护了八路军在华北敌后就位,减轻了敌人对我们的压力,为敌后战场的开辟创造了一定的条件。当然,八路军、新四军向敌后的挺进和敌后战场的开辟,也是对正面战场的有力支持和配合,因为“这种挺进是在敌人战略进攻阶段上我方的反进攻”。它阻止敌人继续长驱向西南、西北进攻,促使相持阶段的到来。
另一方面,在战略防御阶段丧失若干土地虽是不可避免的,但正面战场丧师失地如此之快,之多,却是国民党主观指导上的失误造成的。敌强我弱是中日战争中的一个特点,但不是惟一的特点。从敌人方面说,它还有许多弱点可资我们利用;从我们方面说,也还有许多优点可以发挥。仅就军事力量看,抗战开始时,国民党军队共有291个师另52个旅,近200万兵力,日本现役兵员仅38万,虽然中国的海空军力量劣于日军,但在南北战场上国民党军队在兵力上都占有优势。日军在装备上虽占有优势,但其在战略和战役指导上也是有懈可击的。毛泽东在总结抗战以来的经验时曾指出日军在指导上的五大错误:逐渐增加兵力,没有主攻方向,没有战略协同,失去战略时机,包围多歼灭少。这些“表现其指挥的笨拙”,因而使我有用自己聪明而有效的动作,在有组织的民众掩护之下,造成敌人错觉,调动敌人就我范围的可能性。但是,敌之弱点与我之优点,国民党都没能很好地加以利用和发挥,以至一退再退,使敌长驱直入。究其原因,是国民党在政略和战略指导上的错误,这表现了国民党在抗战中的局限性。关于这个问题,拟在后面一并分析。
二
日军占领武汉、广州后,随着战局的扩大和战线的延长,使其兵力不足、资源匮乏、财政困难的弱点日益显露。中日战争趋向长期化。日本决策者也不能不承认其迅速亡华计划的破产,认为“解决中国事件并非如此简单,国民政府现拥有240师,其外尚有游击队100万以上。如何解决此巨额之军队,如何对付国内之经济问题,及如何应付第三国之态度,均为棘手之问题。因此欲求得彻底解决中国事件则至少需时五年至十年之久”。这时,日军统帅部确定以“确保占领区”为今后主要任务,并划定由包头经黄河下流、黄泛区、庐州、芜湖、杭州一线以东为治安区,以足够兵力恢复这一区域的治安,而作战地区则限定在安庆、信阳、岳州,南昌之间的狭窄区域内,强调“今后在无特别需要,不再扩大占领区”。这样,日军基本上停止了对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抗日战争进入了战略相持阶段。
这时,日本侵略者为了摆脱长期陷于战略被动的态势,及早结束在中国的战争,对国民党采取了以军事打击和政治诱降兼施并用的方针。1938年11月3日和12月22日,日本政府的近卫首相连续两次发表声明,阐述所谓调整日中关系的新方针,改变了1月16日第一次近卫声明中关于“不以国民政府为(谈判)对手”的方针。1939年9月日在南京成立了以西尾寿造大将为总司令的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而西尾来华的一个重要使命即是“解决事变第一,作战第二”。
对于这一时期国民党的抗战及其政策也要作全面的具体的分析。应该指出,日本政府策略上的变化和这时英美策划的“东方慕尼黑”活动,很快在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得到了反映。1938年12月,亲日派的汪精卫集团公开投敌叛国,1940年3月又在南京成立了全国性汉奸政权。英美派的蒋介石集团则开始了其政策上的变化,逐渐将其重点由抗日转移到反共反人民。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就是这个转变的重要标志。在五中全会上,第一,它虽仍申言抗战到底,以期获得最后胜利与建国之成功,但又把“抗战到底”的含义解释为“恢复七七事变以前的原状”;第二、它虽然仍提出继续联共抗日,但又通过了“防共、限共、溶共”的方针。这表明国民党的妥协和反共倾向有了增长,这和抗战初期的情况相比较,确是后退了。
但是,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虽然开始出现消极避战,保存实力的意图,但仍然在支撑着正面战场,维持持久战的局面。1938年11月蒋介石在湖南南岳主持的军事会议,改变了过去所谓三期抗战的提法,认为武汉失守后中国抗战进入第二期,提出第二期抗战要政治重于军事,民众重于士兵,精神重于物质,游击战重于正规战;决定以三分之一部队配备在敌后担任游击,三分之一部队在前方抗战,三分之一到后方整训;调整了指挥系统,重新划分了战区,全国划分为包括苏鲁、冀察两个游击战区在内的共十个战区。虽然进入敌后的部队后来主要是用来对付共产党的,但这次会议的部署基本上完成了由战略防御到战略相持的转变。这时中国抗战出现了以共产党为领导的华北敌后战场和以国民党政府为主体的华中、华南正面战场,两个战场虽然在作战指导和战役上是各自进行的,但在战略总体上仍然是互相配合和互为条件的。
从武汉失守到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期间,日军对国民党战场发动了几次规模不等的战役性进攻,这些攻击不是以攻城掠地为主要目标,而是以摧毁中国继续抗战的力量,掠夺战争资源,控制交通线等为主,企图通过军事压力,迫使中国屈服。在这期间,1939年进行了海南岛、南昌、随枣、桂南和第一次长沙战役,1940年进行了枣宜战役,1941年进行了豫南、晋南、上高和第二次长沙战役。日军虽然在南昌、枣宜、豫南等战役中取得一些胜利,但由于日军已无力进行大规模的战略性进攻,因而战局没有大的变化,双方基本上保持着相对固定的作战线。
在这期间国民党军队仍表现了一定的作战能力,并取得了一些战役的胜利。如第一次长沙会战,前后近一个月,毙伤敌2万多人,迫使敌退到原来阵地;又如上高战役,原来敌决定在其主力三十三师团等部调往华北之前,对南昌方面的国民党第九战区部队发动一次进攻,结果遭到中国军队的痛击,伤亡两万多人,北调计划被打乱。此外,1939年11月至1940年3月,国民党军队还进行了一次较大规模的“冬季攻势”。这次攻势作战,在华南、敌曾在11月间占领南宁,攻陷战略要地昆仑关。12月下旬,国民党军队在白崇禧统一指挥下,向昆仑关发起反攻,经过激战,毙敌中村旅团长以下4000余人,于12月31日收复昆仑关。在华中,国民党军队以七八十个师的兵力进行攻势作战,历时40多天,给敌以一定的打击。在华北,傅作义部曾于1939年12月一度攻入包头,次年2月收复五原。这次“冬季攻势”是正面战场惟一的一次大规模反攻作战,它对于打击敌人,坚持抗战起了积极的作用。但它取得的实际战果不大。这次攻势作战曾使日军不得不重新估计中国抗战的力量,据日本防卫厅研究所战史室编《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记载,它承认“深感敌尚强大”,“证实敌人仍有二百万兵力”。但又说在如此大规模的攻势中,它没有克复任何要地,而且蒙受了极大的打击。从此以后国民党军没有进行过这种大规模的攻势作战。
应该指出,这时国民党实行的消极避战、积极反共的政策也严重影响和削弱了国民党军队的战斗力。例如1941年1月的豫南战役,日军就是利用国民党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之机进行的。1月上旬,华中日军得悉汤恩伯第三十三集团军正在东进,当时汤部位于信阳以东的遂平至项城一带,于是判断其东进目的在于进攻安徽的新四军,认为这是歼灭汤部主力的极好时机。敌迅速调动三个师团兵力分三部向豫南进犯。战役从1月下旬开始,半个多月时间,敌攻占确山、遂平、南阳、汝南、上蔡,项城等十余县城,汤部损失严重。又如,1941年日本中国派遣军根据其大本营《对支那长期作战指导计划》,确定以“加强占领区的治安”作为本年度的一个主要目标,华北日军为改善山西“治安”,决定发动晋南战役(中条山战役),以击破卫立煌的第一战区主力。5月间,日军集中六个师团又三个旅兵力向晋南等地进攻。国民党在这里有20多个师的兵力,虽然守卫部队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像师长王竣、寸性奇等都壮烈殉国,但由于消极避战方针的影响,部队很快渡过黄河,全部退出了中条山地区。在20多天作战中,部队损失惨重。据日本方面的统计,国民党军队死亡约42000人,被俘约35000人。
从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中国人民的抗战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是抗日战争发展的一个新时期。
1941年12月8日,日本偷袭美国在太平洋最大的海军基地珍珠港,同时进攻英、美、荷等国在西南太平洋的属地。太平洋战争发生后,虽然英美等国在开始时陷于十分被动的局面,但总的形势是对中国抗战有利的。这是因为,由此正式形成了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以1942年1月1日由中苏美英等26国联合签署发布的《联合国家共同宣言》为标志),中国人民抗战事业得到更多更广泛的国际同情和援助;同时太平洋战争爆发也宣告了西方帝国主义绥靖政策的彻底破产,美国为重新取得太平洋的优势,也要仰赖于中国战场,因而从这时起美国对中国的军事和经济援助大大增加,这一时期罗斯福给蒋介石的信件也不乏友好和恭维之词。1942年1月,在美英两国的建议下,设立了中国战区统帅部(含中国、泰国、越南和缅甸北部),蒋介石为统帅,史迪威为参谋长,统一指挥这一地区联合作战。美国的参战和“美援”的增加,对于一贯依赖英美的国民党是一个很大的鼓舞,也进一步坚定了蒋介石集团的抗战决心。
从这时起,中国抗战不仅在战略上配合和援助了太平洋战争,并且也在战役上支援和参加了英美军队在南方的作战。
珍珠港事件后不久,日军为配合其在东南亚地区的进攻,防止中国军队南移,集中2万兵力发起第三次长沙战役。国民党军队先后有14个军参加会战,给敌以重大杀伤。战斗持续23个昼夜,据国民党方面统计,此役毙伤敌56000人。长沙会战胜利在国内外产生很大影响,美国海军部长诺克斯发表告中国人民书称“这是所有同盟国家的胜利”。
为配合英美盟军,国民党政府还派远征军入缅作战。1942年初,日军准备攻占缅甸。应驻緬英军司令韦维尔要求,国民党政府先派空军志愿军赴仰光协防(未到,仰光已陷),后又派由三个军组成的中国远征军援緬。入缅作战的目的是配合英军,保卫滇缅路,维持我国的对外交通线。10万远征军在异国顽强抗击日军,掩护英军撤退。历时12天的同古一战,毙敌5000,伤无数。日军大佐横田日记称“南进以来,从未遭受若是之劲敌,劲敌为谁,即支那军也”。但作战后期,由于盟军指挥协同失当等原因,远征军作战遭到失败。5月,远征军一部退入印度,大部回到国内。师长戴安澜和数万壮士战死他国战场。1943年4月,退回云南的远征军与增派的部队组编为滇西远征军,撤退到印度的远征军同国内新派去的部队改编为中国驻印军。10月,中国驻印军五个师从印度进入缅甸北部,同日军展开反攻作战。1944年5月,滇西远征军17个师越过怒江,向西进攻,翌年1月在畹町与中国驻印军会师,打通了中印公路。在缅北作战中,中国军队收复大小城镇50多处,歼灭日军31000多人,为收复缅甸,配合盟军作战作出了贡献。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作战的指导中心逐渐移向南方对英美的战争,但中国仍是其所谓“大东亚圣战”的重要战场,用于中国战场的兵力仍在60万左右(如1943年侵华兵力比其在南方作战兵力约多出一倍)。这时候侵华日军仍以确保其占领区为主要任务,对国民党正面战场的军事行动则主要以太平洋战争的战略需要为转移。1942年4月,美机从太平洋上的航空母舰起飞,首次轰炸日本本土东京、神户等地,引起其国内一片惊慌。美机返航至中国浙江境内降落。这时中国沿海的一些机场确成为美国保持空军优势的重要基地。日本大本营为使其国内免受空中威胁,确保太平洋战争的顺利进行,遂命侵华日军以打通浙赣铁路、破坏沿途机场为目的,发动浙赣战役。从5月开始,日军以10万之众发动进攻,国民党军队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抵抗,给敌以相当的杀伤,但由于某些高级将领消极避战、保存实力思想严重,指挥失当,至7月,敌先后占领了48座县城,打通了浙赣路,并彻底破坏了玉山、衢州、丽水等机场及附属设施。日军大本营认为作战“目的已达”,遂按照不扩大占领区的方针,下令除确保金华及附近的地区外,恢复原态势。是役,中国军民伤亡约达25万人。这是日军为配合太平洋作战(正是日军准备进攻中途岛之际)向中国正面战场发动的一次进攻。
从1942年下半年开始,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这年6月,美国海军在中途岛海战中,重创日海军联合舰队;8月,美军攻占日军在南太平洋上具有重要战略价值的瓜达尔卡纳尔岛,从此盟军在太平洋战场逐渐转入了战略反攻。这时日本为摆脱困境,企图收缩战线,尽快结束中国战争,以便集中对付太平洋战争。它在政治上加强了所谓“招抚”政策,一面利用国民党内部派系矛盾,分化、拉拢军政要员,一面对蒋介石作出让步,以同意恢复七七事变前的状态为诱饵,要蒋政府与英美断绝关系。同时在军事上继续施加压力,企图进一步控制长江上游及洞庭湖主要产粮区,进而对重庆造成威胁之势。日本的“招抚”谋略曾收到一定的效果,国民党重要将领如吴化文、孙殿英、庞炳勋等都是在这时投敌的。但由于这时国际形势已发生重大变化,蒋介石对日和谈已表现冷淡,因而日本企图尽快结束中国战争,以便用侵华兵力去挽救太平洋战场的颓势,是根本不能实现的。至于1943年日军对正面战场发动的鄂西战役和常德战役,也没能够取得新的进展,双方仍基本上保持了原来的态势。
但是,随着太平洋战争的胜利发展,蒋介石集团依赖美英保存实力,坐等胜利的思想更加严重,抗战后期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和反共反人民政策,不仅严重削弱了中国抗战的力量,而且也使它的大批部队丧失了战斗力。1944年国民党军队在豫湘桂战役中的大溃败,就是国民党推行对日消极避战和积极反共政策的结果。
1944年,美军采取越岛进攻战术。7月占领塞班岛,把战争推进到离日本本土只有二千公里的海域。日本东京内阁被迫总辞职。日本为了扭转其在太平洋战场的不利战局,决定对中国正面战场发动一次战略性进攻,目的是要打通平汉铁路南段、粤汉铁路和湘桂铁路,开拓一条由朝鲜、中国东北,贯通华北、华中、华南直至越南的大陆交通线,以挽救孤悬南洋的日军,并摧毁美国在中国的空军基地。为此,日军作了周密的准备,大力扩编军、师团,补充兵员,并从国内和关东军抽调部队参战,整个战役先后投入了五个军十六个师团和若干旅团,总兵力达四五十万人。在越南和缅甸的日军也采取了相应的行动。日军大本营把这次豫湘桂战役称作“打通大陆交通作战”,代号为“一号作战”。整个作战从1944年4月中旬至12月下旬,包括河南战役和湘桂战役。这次虽然是日本侵华战争以来最大的一次攻势,但从总的看,日军已丧失了战略主动权,整个战局对我有利,在整个作战中国民党军队先后投入100多万兵力,占有优势,且在战役前后,敌后八路军都进行了积极的配合,这同抗战初期的形势已大不相同。但是,国民党长期执行的避战、反共政策,却使它的部队丧失了战斗力。如担任河南正面防御和黄河河防的第一战区副总司令汤恩伯(总司令蒋鼎文)所部30余万人,经营河南数年,以反共、扰民为能事,结果在日军10余万兵力的进攻下,除非嫡系部队(如孙蔚如、马法五、刘茂恩等部)进行一些比较认真的抵抗外,而号称精锐的汤恩伯部队却一触即溃。河南战役前后38天丢失城市38座,折兵过半。在湘桂战役中,主要进行了衡阳保卫战,从6月22日至8月7日,坚守危城47天,连续打破日军两次总攻击,打得顽强、出色,但最后却以守城指挥第十军军长方先觉叛国投敌而告终。在豫湘桂战役的短短八个月中,日军长驱直入,从河南一直打到广西,并继续沿黔桂线推进到贵州独山一带,直逼重庆。国民党军队损失兵力六七十万,丢失包括146座大中城市的20万平方公里土地,7个空军基地和36个飞机场,使6000多万同胞沦于敌人的铁蹄之下。应该指出,日军虽然打通了平汉、粵汉和湘桂铁路,但因运输材料缺乏,大陆交通线始终未能全线通车,它的战略意图实际上未能实现。相反,由于战线的延长,分散和牵制了大量日军,使这次战役不但不能挽救其日趋恶化的总态势,却给中国抗日军民的反攻造成了有利时机。
总之,相持阶段到来以后,国民党抗战的消极方面开始突出,特别是抗战后期它的危害作用更加明显。但是,由于国际和国内各种因素的制约,这时的国民党统治集团仍然是具有既抗日又妥协,既抗战又消极避战,既联共又反共这样两面性的。在战略相持阶段,国民党军队进行了18次会战,并两度赴缅作战,仍牵制了约占40%左右的侵华日军,维持了持久抗战的局面。在整个八年抗战中,据国民党政府公布的材料,共作战4万多次,其中会战22次,重要战斗1170次,毙伤日军237万。因此,仅就抗战而言,国民党的积极作用是其基本的方面,是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三
七七事变后,国民党接受了中共倡导的团结抗战的主张,这是国民党历史发展中的一个进步,基合乎民族大义的行动。“当时全国人民,我们共产党人,其他民主党派,都对国民党政府寄予极大的希望,就是说,希望它乘此民族艰危、人心振奋的时机,厉行民主改革,将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三民主义付诸实施。”抗战一开始,中共就制定了国共两党长期合作的方针,希望国民党彻底改变十年内战时期的错误政策,以实现共同抗日与共同建国的目的。
如前所述,国民党在八年抗战中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它并没有如全国人民所希望的,彻底弃旧图新,相反却重蹈过去的一套错误做法,这不仅限制了它在民族战争中应有作用的发挥,削弱了全国军民的抗战力量,并且成为最终导致国共两党关系破裂,使它自己丧失人心的深刻原因。这恰恰表现了它作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政党在民族战争中的阶级局限性。这种阶级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表现在政治上它执行一条反人民的片面抗战路线。抗战初期毛泽东就指出:当时“参战的地域虽然是全国性的,参战的成分却不是全国性的。广大的人民群众依然如过去一样被政府限制着不许起来参战,因此现在的战争还不是群众性的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战争而不带群众性,是决然不能胜利的。”因而,关于如何抗战问题,即全面抗战还是片面抗战,成为抗战时期国共两党争论的主要问题,也是关系到抗战前途的根本问题。应该看到,国民党中的多数人是具有爱国的民族意识,是有抗战的热情和决心的,但它的统治集团则主要是从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出发,被迫参加和坚持抗战的,它的抗日是具有不彻底性和妥协性的。国民党蒋介石集团虽然在抗战初期有条件地承认了人民的某些民主权利,但由于它畏惧人民力量的壮大,基本上是把解决中国抗战问题的希望寄托在英美等国身上,因而不愿利用和发挥民族解放战争中的有利条件,拒绝中共和其他民主党派关于实行全面的全民族抗战的主张,力图把抗日战争局限于单纯的政府和军队抗战。这是国民党丧师失地的深刻的政治原因。
相持阶段到来后,由于中共领导的人民抗日力量迅速壮大,在华北和华中开辟了广大的敌后根据地;由于日本基本停止了对正面战场的战略性进攻,对国民党更多地采用政治诱降的策略;由于国民党已将其主力转移到西南后方,又有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畏惧和仇视人民力量的情绪迅速增长,逐渐把注意力从日本帝国主义身上移到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身上来。这时国民党采取了对日消极作战、对内积极反共的政策,它不但“将抗日初期人民和各抗日党派争取得来的某些权利,一概取消”。而且还不断制造反共的军事磨擦。据统计,从1938年10月至1944年3月,六年多的时间,国民党使用约190万军队,制造反共磨擦事件约2500多次,其中并有三次反共高潮。武汉失守后国民党曾决定抽调三分之一兵力到敌后开展游击战争,这个决定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是,进入敌后的部队却主要被用来对付共产党,特别是1941年以后,蒋介石采取罪恶的“曲线救国”政策,指使敌后部队投降敌方,以伪军旗号进攻解放区。据统计,进入华北,华中敌后的国民党军队不下100万(1941年在华北约有80万,华中约有20万),除被敌人消灭或撤回后方夕卜,投敌的竟达50万人(占伪军总数62%),到1944年留在华北敌后的不过二三万人。这样,不仅严重削弱了抗战力量,而且正是由于国民党坚持一党专政及其错误的政策,导致了它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严重困难,日渐失去了民心。
其次,在军事上采用消极防御战略并沿袭腐败的军事制度。在敌强我弱的军事形势下,我们作战的基本方针应采取“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以运动战为主,以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为主要目的。而国民党军队的战略防御,始终把阵地防御战放在主要地位,企图以单纯防御阻止敌人的进攻。这种消极防御的方针,即不积极寻找和利用有利战机灵活机动地打击敌人有生力量,不敢把主力用于侧面,采取迂回包围的战法,调动和分散敌人,达到各个歼敌的目的,而是在预定的阵地上摆出决战架势,等待敌人进攻,在固定的地域与敌人拼消耗。这就置自己于被动地位,既不能为进攻战役和战略反攻创造条件,又使敌人的长处得到发挥。八年抗战中正面战场22次大的会战,绝大多数都是这种阵地防御战。正是“这种笨拙的战略,就使得前线将士英勇的奋斗不能获得应有的战果”。
国民党军队在作战指挥上的错误,还和它腐败的军事制度紧密相关。国民党军队内部派系复杂,上下争权夺利,互相排挤倾轧,在战场上各自保存实力,互不配合。国民党军事上实际是军事寡头制度,在战略和战役指挥上,蒋介石独揽军权,一切由个人说了算,使正确意见得不到采纳。他甚至进行越级指挥,各级指挥官形同虚设。一些高级指挥官患有严重的恐日病,腐朽无能,敌未至而自溃和临阵逃脱的丑行并不鲜见。这连蒋介石也不得不承认,他曾说无论在上海或其他战场,每次后退,都是我们高级将领,判断敌情不明,乃至贪生怕死,不敢指挥部队,先自脱逃所以不能掌握部队,如此,你当主官的先违犯军纪,犯了临阵脱逃之罪,叫部下如何不溃散,不犯罪呢?这是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国民党战场一个方面的情况。所以,毛泽东曾指出:“现在国民党军队的制度还是老制度,要用这种制度的军队去战胜日本帝国主义是不可能的。”“广大的将士虽有忠勇之心,但束缚于旧制度,无法发挥其积极性。”
再者,在对日态度上表现为既抗日又妥协动摇。抗战八年,国民党政府始终不敢依靠和发动人民抗战,最初它把制止日本侵略的希望寄托在英美苏各国的干涉上,随后又间接或直接地同日本秘密谈判,进行“和平”运动。它是一面抗战,一面又是随时准备妥协。1937年12月,国民党政府就响应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的“和平”调停;1938年国民党政府外交部主管对日事务官员董道宁、高宗武奉命秘密赴日,沟通“和平”渠道;1939年3月和6月日蒋代表先后在香港、澳门秘密会谈,并曾达成举行板桓征四郎、蒋介石长沙会谈的协议;1940年至1941年,日本又通过司徒雷登(燕京大学校长)奔走于北平、重庆之间,进行“和平”搭线;1944年,日本通过释放吴开先(曾任国民党中组部副部长、上海市社会局局长),再次向重庆试探;直到1945年7月,当日本败局已定时,仍有日军代表与国民党高级将领在河南新站集的密谈。
总之,国民党在八年抗战中,做了许多错事和坏事,而对内反共反人,民和对日妥协动摇,则集中表现了它作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政党的阶级局限性。国民党在抗战中后期曾积极地进行反共活动,但终未酿成全面内战,曾多次谋求对日妥协,但也未成为事实。这从根本上说,是因为中日民族矛盾始终是主要矛盾,日本的侵略活动和它对国民党的苛刻的“和平”条件,既损害英美的在华利益,也威胁着国民党的统治,这就不能不对国民党的反共和妥协活动起着制约的作用;同时,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的反动方面采取了正确的斗争策略,妥善地处理了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关系,既使人民抗日力量在斗争中得到了发展,又限制了国民党的反共和妥协的企图,从而维护了国共合作的局面。
抗战八年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坚持抗战、团结、进步,是争取这场民族解放战争胜利的要求,是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愿望,国民党在这方面曾做过一些利国利民的好事,因而得到人民群众的一定的谅解和拥护。但是,国民党统治集团并没有把它贯彻到底,而是采取错误的政策,违背了历史发展的要求和人民的根本愿望,从而使自己走向了反面,这对国民党来说不能不是一个重要的教训。
历史经验还告诉我们,国共两党是中国的两大政党,两党合作有利于国家民族。毛泽东曾多次热情地评价国共合作的意义,他说:“中国军队在民族公敌面前,互相忘记了旧怨,而变为互相援助的亲密的朋友,这是中国绝不会亡的基础。”第二次国共合作取得的抗日战争的辉煌胜利和随后发生的历史曲折,证明了“联共则荣,反共则衰”的真理,这对今天仍然是十分有益的历史经验。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论文集》,1985)
列宁曾指出:“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研究历史的重要原则。因而我们要全面客观地分析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历史作用,既实事求是地评价它在抗战中的功绩,又实事求是地指出它的历史局限性,这样才有助于我们正确地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也有助于我们树立正确的历史观点。
一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开始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全面侵华战争。当时,中共中央通电全国,首先指明了这次事变的严重性质和坚决抗战的必要性。在日本灭亡中国方针的威胁下,在全国人民抗日浪潮的推动下,国民党开始改变过去的不抵抗政策,转而采取比较努力抗战的态度。
七七事变发生后,国民党政府虽然仍想通过外交谈判的途径力求避免“事态扩大”,但同时也对事变采取了比较强硬的立场。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提出解决卢沟桥事件的四个条件:(1)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之完整;(2)冀察行政组织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变;(3)中央所派地方官吏不能任人要求撤换;(4)第二十九军现在所驻地区不能受任何约束。谈话虽仍希望通过和平的外交方法解决,但表示中国已临到“最后关头”,“如果战端一开,就是地不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这个谈话的基本精神是好的,正式表明了中国政府的立场。这时日本已大量增兵关内,公开抛弃了所谓“不扩大方针”的欺骗宣传。7月30日相继占领北平、天津,8月13日又开始进攻上海。8月15日,日本正式成立以松井石根大将为司令官的上海派遣军,并下达了全国总动员令,于是开始了对中国的大规模战略进攻。
在这种情势下,中国政府采取了相应的措施。8月14日,中国政府发表《自卫抗战声明书》,宣告“中国决不放弃领土之任何部分,遇有侵略,惟有实行天赋之自卫权以应之”。15日,蒋介石下达总动员令,20日蒋自任陆海空军大元帅,决定将政府军事委员会作为战时最高统帅部,并将前线省份划为四个战区。与此同时,经中共中央一再呼吁和敦促,国民党对联共抗日也采取了积极态度。9月23日,蒋介石为中共关于国共合作宣言的公布发表谈话称在存亡危急之秋,更不应计较过去之一切,而当使全国国民彻底更始,力谋团结,以共保国家之生命与生存。使国共第二次合作得以实现,为实现全民族抗战创造了条件。
毛泽东曾指出:“国民党在1937年和1938年内,抗战是比较努力的,同我党的关系也比较好,对人民抗日运动虽有许多限制,但也允许有较多的自由”。这是符合历史实际的正确评价。在战略防御阶段,国民党及其军队的抗战是比较积极努力的,正面战场是有历史功绩的,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这个阶段,国民党正面战场是抗战的主要战场。
从一般军事学上说,在通常的情况下,正面战场总是担负着主要的作战任务。由于国民党实行的抗战路线和日军对华作战重点的变化,使国民党战场在抗战不同阶段所起的作用有很大的区别,但是,应当肯定,在抗战初期,国民党正面战场确是担负主要战场的作用。
从敌人方面看,这时日本凭借其兵力和军备上的优势,在战略上强调“速战速决”,企图集中兵力在最短时间内摧毁中国军队的抵抗能力,迫使中国政府屈服,实现其独占中国的目的。七七事变前后,日本军国主义者一再扬言三个月之内就可解决中国,当时的杉山陆相甚至叫嚣“支那事变可以在一个月内完全结束”。战争开始后,不断增加其侵华兵力,到1937年9月,日军侵华兵力已超过战争初期所预定的最高限额11个师团,达到了14个师团。它同时在华北和华东展开进攻,然后南下华中,幻想速战速决。到1938年1月16日日军占领南京后,日本政府发表声明(即第一次近卫声明):“帝国政府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谈判)对手,而期待真正能与帝国合作之中国新政权的建立与发展。”这些都说明,这时期日军作战是以国民党政府为主要对象,其目的是要摧垮国民党军事力量,迫使中国投降。
从国内方面看,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倡导者、组织者,对团结抗战的实现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有着良好的政治和军事素质。但在战争开始时,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只有几万人(当时在华北前线的八路军共32000人),武器装备很差,还不能给敌造成足够的威胁。而这时国民党是第一大党,处在执政地位,它参加抗战后,在一定程度上起了团结全国抗战力量的作用。1937年8月初,国民党政府在南京召开国防会议。中共代表朱德、周恩来、叶剑英应邀与会,共商国防问题。此外,广西、四川、云南、山西等地的地方首领白崇禧、刘湘、龙云、阎锡山等都参加了。原来国民党中央与地方实力派之间矛盾很深,互相猜疑,七七事变发生后,蒋介石曾电邀李宗仁、白崇禧到南京共商大计,龙云、刘湘曾电李、白劝阻,“未可轻易入京,万一抗日不成,反而失去自由”。可见疑虑之深。但在民族敌人生死威胁面前,使他们暂时捐弃前嫌,同意联合抗战。正如李宗仁所表示的:“今日的局势只有两条路可循,不是抗战图存,便是投降亡国。”表示要秉“先国难而后私仇”的大义,拥护中央参加抗战。因而这次作为抗战决策的南京国防会议,结束了国民党内部四分五裂,各自割据一方,内战迭起,纷争不已的局面。此后,各地军队陆续开赴前线作战。抗战初期,蒋介石先后调动近200万军队,在华北、华东和华中等地对日作战,他们除蒋介石的中央系统的张治中、朱绍良的第五集团军,陈诚、薛岳的第十五集团军,罗卓英的第十九集团军,卫立煌的第十四集团军,胡宗南的第十七军团,汤恩伯的第二十军团等外,还有许多地方实力派的部队,主要有:原东北军的于学忠五十一军,何柱国骑二军,廖澄流五十七军,刘多荃四十九军;原冯玉祥西北军旧部宋哲元的第一集团军,孙连仲的第二集团军,韩复榘(后为孙桐萱)的第三集团军;山西阎锡山部傅作义的第七集团军,商震的第二十集团军;广西李宗仁、白崇禧部李品仙的第十一集团军,夏威的第十六集团军,廖磊的第二十一集团军;四川刘湘的第二十三集团军,邓锡候的第二十二集团军,刘建绪的第十集团军,潘文华的第二十八集团军;广东余汉谋的第十二兵团,叶肇的六十六军,邓龙光的八十三军;云南龙云部卢汉的六十军,孙度的五十八军等等。这时开赴华北前线的八路军,以自己英勇顽强的战斗,积极配合了正面战场作战。当时《大公报》社评曾称:“中国此一战,征调兵队及于全国,凡奉命赴战的军队没有不勇敢,没有不拼命的。”总之,抗战初期国民党正面战场作为主要战场的作用是显见的。
第二,在这一阶段,国民党军比较积极认真地进行了正面防御作战,并打了一些硬仗。
抗战开始后,日军处战略进攻态势,中国处战略防御态势。南京国防会议根据敌强我弱的形势,确定实行“持久消耗战略”的国防方针,即以空间换取时间,以持久作战消耗敌人;同时根据日军主要以华北为进攻方向,因此决定在平汉、津浦两路沿线地区设置三道防线,以正面的阵地防御战来保守城市和战略要地。从全面抗战开始到武汉广州失守的十五个月战略防御阶段,国民党军队在华北、东南及华中两大战场开展正面防御作战,据统计,国民党军在这期间同日军进行重要战役战斗270多次,歼敌77万。其间著名的有忻口(太原)、淞沪、徐州、武汉等四次大的会战,并取得了台儿庄战役的胜利。
忻口(太原)会战,是华北战场上进行的一次较大规模的战役。
1937年7月30日,日军占领北平、天津后,即向华北纵深挺进。这时在华北战场上国民党军队约70万人。担负平汉线防守的为刘峙的第二集团军,担负津浦线防守的为宋哲元的第一集团军,担负平绥线防守的为汤恩伯的第十三军和高桂滋的第十七军。8月31日,日军正式编组以寿内寺一大将为司令官的华北方面军,辖八个师团,分兵三路沿平汉、平绥、津浦铁路线南下发动进攻。敌将主力置于平汉线方向,企图“迅速消灭河北省中部敌人”。国民党军队在保定、沧州一线节节抵御。由于守将刘峙畏敌退却,敌连陷固安、涿州后,9月24日占领保定,使原来准备在保定一线组织防御的计划未能实现。10月10日,敌攻陷华北重镇石家庄。随后,日军对平汉线取守势,将进攻重点转向山西,并以一部兵力进入正太铁路。而进攻平绥线的日军也于8月27日攻占军事重镇张家口,9月12日占领大同,敌坂桓第五师团则南下进入山西的浑源、灵丘一线,于是晋北告急。10月1日,日军部正式下达攻取太原的命令,并作出由晋北和晋东沿同蒲、正太两铁路线分进合击的部署,企图一举夺取山西,进而解决华北战局。
国民党政府曾提出“确保山西”的方针,当晋北告急时,阎锡山急令傅作义赶赴前线指挥,南京政府也急调卫立煌部由河北驰援晋北。中国部队部署平型关及内长城一线。总兵力六七万。这时奉命开赴山西作战的八路军一一五、一二〇师,到达雁门关、平型关一带,协同友军作战。9月25日,一一五师首战平型关,歼敌精锐坂垣师团一部千余人,取得华北抗战以来第一次胜利,极大地鼓舞了中国军民的抗战信心。敌在平型关受阻后,转而进攻平型关与雁门关之间的茹越口,中国守军经过激战后,于9月底全线后撤,山西内长城防线被突破。
10月初,为保卫太原,挽救危局,国民党第二战区先后集中十六个师十余万人,组成三个防御兵团,以卫立煌为前敌总指挥,在太原以北忻口地区组织会战,同时由孙连仲等部在太原娘子关一线阻敌西进,配合晋北主力决战。从10月13日起,敌5万余众向忻口阵地猛烈进攻,中国守军浴血奋战20多天,坚守住阵地。这时,八路军各部在敌后积极配合,五师、一二〇师频频出击,破坏交通,截断日军后方补给线,并一度占领雁门关,使敌弹药补给十分困难;10月19日,一二九师夜袭阳明堡,击毁敌机20余架,有力地配合了友军作战。忻口会战显示了中国军民抗战的威力,在近一个月的作战中,使敌无法前进一步,伤亡达3万多人。中国官兵牺牲也达10万之众,其中包括第九军军长郝梦龄、第五十四师师长刘家骐等。东线娘子关守军也进行了英勇抵抗,但因兵力分散,在强敌猛烈袭击下,10月26日娘子关陷落,守军全线撤退,敌进而逼近榆次、太原。娘子关失守后,忻口阵线动摇。11月2日,阎锡山下令忻口守军撤退。11月9日,太原失守。从此,华北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规防御战已基本结束,进入了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抗日游击战争阶段。
淞沪会战。这是正面战场进行的一次最艰苦激烈的会战。
当平津战事正激烈进行之际,日军又策动对上海的进攻,企图钳制中国军队主力,配合夺取华北,并进而占领沪宁,迅速迫使国民党政府屈服。八一三事变发生后,蒋介石即令在沪宁线驻守的张治中率两师兵力增援上海,痛击入侵之敌,同时任命冯玉祥为第三战区司令官,负担淞沪战场作战指挥(9月中旬以后蒋介石兼三战区司令官,顾祝同为副司令官,负责前线指挥)。国民党政府先后从各地调集到淞沪前线的军队达22个军50余师,总兵力为70万人。开始,日军以海陆军1万多人依靠海空优势火力的掩护,在上海北部地区登陆,向闸北等地进攻。由于兵力不足,在中国军队严重打击下,日军在狭小范围内无法展开,处于被动局面。8月底以后,日军由国内和台湾等地大量增兵上海,总兵力达30万人。双方战斗日趋激烈。敌我双方在宝山、罗店、大场、北站、浏河、吴淞、蕴藻浜、刘行、闸北、苏州河岸等地展开争夺战。战斗最激烈时,中国军队每小时伤亡达千人,主力各军都补充了四五次,下级军官伤亡达三分之二,旅团级军官伤亡也过半。日本大本营称,日军开始参战的两个师团(第三、第十一师团)人员已伤亡殆尽,全部以新的兵员补充,为日俄战争以来从未有过的损失。原来日军曾扬言十天即可占领上海,但却被中国军队拖住3个月之久。上海作战后期,由于日军大量增兵,而中国增援难继,已渐陷于被动地位,这时蒋介石为照顾所谓国际影响,仍一再下令坚守,致使前方损失惨重。11月初,日军在杭州湾金山卫和济河两翼登陆,迅速切断沪杭铁路线,9日攻陷松江,使中国军队腹背受敌,整个防御部署被打乱。为保存主力免遭围歼,蒋介石被迫下令全线撤退。11日,上海失陷。
此役,日军伤亡达6万人,中国军队伤亡近20万人。历时三月的淞沪抗战,有力地击破了日军“三月亡华”论,充分显示了中国军民抗战的力量。
日军占领上海后,随即沿沪宁铁路进攻南京。至12月初,敌已从东、南和西南三面进逼南京。国民党军队由于仓促组织防御,十几万部队又死守孤城,13日南京就被敌攻陷。日军在南京制造了亘古罕见的大惨案,30万和平居民惨遭屠杀。
台儿庄战役。这是徐州会战中的一个重要战役。
日军实现占领华北和宁、沪、杭后,遂将作战重点转向华中,企图首先夺取徐州,打通津浦路,使南北两个战场打成一片,然后集中力量攻取武汉。其时,沿津浦路南下的华北日军(第十师团)已占领济南,进抵兖州、济宁一线,敌第五师团则沿胶济铁路进犯,华北日军第十三师团也沿津浦线北犯,攻占了淮河北岸蚌埠等地。这时担任津浦路和徐州一线防御的是李宗仁为指挥的第五战区部队,加上增援的汤恩伯、孙连仲等部,总兵力达60万人。
1938年3月中旬,在敌第二军司令官西尾寿造指挥下,以第五师一部直趋临沂,第十师团向滕县等地进攻,企图会师后合攻台儿庄,消灭运河以北中国军队主力。进攻临沂之敌,受到守城庞炳勋部顽强抵抗,随后又得到增援的张自忠部配合,激战五昼夜,歼敌四千余,迫使日军退守莒县,从而粉碎了日军第五、十师团合攻台儿庄的计划。滕县守军在一二二师师长王铭章指挥下,与敌激战三昼夜,全部壮烈殉国。3月23日,敌第十师团开始进攻台儿庄。台儿庄位于徐州东北三十公里,扼运河的咽喉,具重要战略地位。李宗仁以一部兵力驻守台儿庄,正面牵制敌人,以主力置敌侧后,伺机歼敌。24日,敌以地面和空中猛烈炮火攻击台儿庄,中国守军奋勇作战,27日敌一部冲入台儿庄,双方展开巷战,反复争夺,战况惨烈,我守城部队伤亡过半。此时,在李宗仁的一再严令下,汤恩伯部由南向北从侧背攻击敌人,4月6日与守城部队发起反攻,内外夹击,大败日军,歼敌两万余人(毙敌七千余,击伤13000余人)。台儿庄战役是国民党正面战场取得的第一个较大的胜利,具有重要的意义。
日军在台儿庄受挫后,4月间即从华北及苏、皖等地调集重兵,合力围攻徐州。至5月初,敌十三个师团30余万兵力分六路进攻,形成了对徐州四面合围态势。为避免主力被歼,李宗仁决定全线撤退,跳出了敌包围圈。5月19日徐州失落。
徐州会战取得台儿庄战役的胜利,随后又保证了主力安全西撤,这从作战指导上说是比较正确的。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在徐州会战进行之际,国民党军副总参谋长白崇禧奉命去徐州协助李宗仁指挥作战,临行前,白曾专请周恩来商谈津浦战场的作战方针。周向他建议:津浦南段以运动作战为主,辅之以游击战,并已令新四军作战役配合,这样在广阔的淮河流域使日军时刻受到威胁,不敢贸然北上;在徐州以北则宜采取阵地战与运动战相结合的方针,守点打援,以达到各个击破的目的。后来在徐州会战中大致采纳了这个建议,在作战方法上比较积极主动,因而取得了成效。这是抗战初期国共合作的一段佳话。
武汉会战。6月15日,日本御前会议正式批准发动武汉战役,接着日军大本营又作出“以初秋为期,攻占武汉”的决定,其主要目的是占领国民党临时政治中心武汉,并配合夺取华南重地广州,进一步从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给中国以严重打击,迫使中国政府屈眼。敌先后集中了14个师团的兵力,以第十一军所属溯长江两岸西进为主攻方向,以第二军在淮河以南策应。国民党则在“保卫大武汉”的口号下,在武汉地区集结兵力100万人以上,以李宗仁的第五战区和陈诚的第九战区实施防御作战。
国民党军主力集中武汉外围沿长江两岸展开,战场遍及皖、赣、鄂、豫四省广大地区。武汉战役从1938年6月12日敌在安庆登陆开始,至8月下旬,主要是外围作战阶段,国民党军依托长江沿岸要塞和大别山麓地区进行了顽强抵抗。7月26日,敌占领九江,随后在长江方面越过了国民党军第一防御地带(鄱阳湖及大别山东麓一线)。8月下旬,日军大本营正式下达攻占武汉的作战命令,于是日军从南北两线分兵五路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国民党军节节抗击,阻敌前进。在武汉会战期间,国民党军同日军大小战斗数百次,并在南浔路、马头镇、富池口、大冶、半壁山、黄石港、田家镇、万家岭等地重创日军。至10月中旬,由于日军已突破国民党军第二防御地带(决战地带),对武汉形成了包围态势,在此情况下,国民党政府军委会于21目决定放弃武汉。25日,武汉失陷。
武汉战役历时四个多月,据国民党方面统计,敌伤亡达10万人以上,基本上达到了“作战四个月,予敌以最大之消耗”的目的,掩护了政府机构和经济文化设施的西迁,使日军速战速决的目的归于破产。
抗战初期国民党正面战场上述的四次大会战,基本上反映了这一时期国民党军队正面防御作战的情况。
第三,广大官兵作战勇敢,表现了中华儿女同仇敌忾,不怕牺牲的爱国精神。
抗战发动后,国民党军队官兵中长期被压抑的抗日爱国精神被激发起来了。同样一支军队,由于战争的目的性不同,会表现出完全相反的精神面貌。国民党军队在抗日战场上,除少数畏敌溃逃外,广大爱国官兵积极主动,浴血奋战,涌现了许多感人至深的英雄业绩。像在淞沪会战中,守卫宝山的姚子青营五百官兵,面对2000日军、30余艘敌舰,20多架飞机和近30辆坦克的攻击,奋勇抗击七昼夜,一次又一次打退敌人的进攻。最后日军施放硫磺弹,燃起全城熊熊烈火,敌军在战车掩护下冲入城内。全营官兵与敌巷战肉搏,激战两昼夜全部壮烈牺牲。当时沪《大美西报》曾著文赞叹此次姚营全部珣城,其伟大壮烈,实令人内心震动而肃然起敬,此非仅为中国人之光荣,亦为全人类之光荣。其伟绩将永垂史迹而不朽。又如,守军八十八师五二四团代团长谢晋元,奉命率五百多人从北站进驻四行仓库,掩护主力从苏州河北岸撤退。他受命后曾以诗明志,写道:“勇敢杀敌八百兵,抗敌豪情以诗鸣。谁怜爱国千行泪,说到倭奴气不平。”他们在人民群众的热情支援下,坚守阵地,奋战四昼夜,击退敌人六次进攻,歼敌200余人,击毁战车两辆,孤军伤亡37人。后奉命退入租界,被迫将武器交给租界当局,人被软禁在胶州公园。在三年多的孤军营生活中,谢晋元仍然励精图治,继续训练军队,准备重上战场杀敌。1941年4月24日,谢晋元惨遭叛徒谋害。国民党军队中的一些高级将领,也同样表现了可贵的民族气节和英勇杀敌的爱国精神。像第九军军长郝梦龄,过去曾参加过内战,痛感“流血千里,人民遭殃”,一度要求解甲归田。七七事变后,他主动请缨北上抗日,并与家人立下遗书,决心拼死在抗日疆场。忻口会战时,他任中央兵团指挥。在他寄出的最后一封家书中曾写道此次抗战乃民族国家生存之最后关头,抱定牺牲决心,不能成功即成仁,为争取最后胜利,使中华民族永存世界上,……故余牺牲亦有荣,为军人者,对国际战士,死可谓得其所矣。“在作战中,他身先士卒,终于履行了自己为国捐躯的誓言。此外,如佟麟阁、赵登禹、刘家麒、王铭章、李必蕃等将军,都先后以身殉国。毛泽东对他们的爱国牺牲精神曾给以很高的评价。赞誉为”崇高伟大的模范。
对于中国军队英勇顽强的抵抗,敌人也不能不感到震惊。如守卫台儿庄的池峰城师官兵,与攻入城内的敌人反复肉搏,血战经旬,在城寨被敌占领四分之三的险恶形势下,仍然死命支撑,最后夺回了失地。敌人目睹此壮烈场面,在战报中曾写道敌于狭窄的散兵壕内重叠相枕,力战而死之状,虽为敌人,睹其壮烈亦为之感叹。又说“尸山血海,非皇军所独有”。
总之,从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到1938年10月武汉、广州失陷期间国民党进行了比较顽强的抵抗并取得个别战役的胜利。但是,从整体上说,正面战场的防御作战是失败的,在仅仅十五个月的时间里,日军长驱直入,很快就囊括了华北、华中大片土地和华南的要地,历次会战也都以失败或退却告终。当然,对于这种情况,也应该给以全面的、客观的分析。
一方面,从根本上说,这是由敌强我弱的形势决定的。由于日本是采取战略进攻方针,中国居于战略防御地位,在战争的一定阶段上,敌能得到一定程度的胜利,我则将遭到一定程度的失败,这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我们在总体战略上,应自觉地采取战略的持久战。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应避免在不利条件下的无把握的决战,勇于实行必要的退却,虽然丧失若干土地,但赢得争取胜利的时间。“这是抗日战争的上策”。从这一方面看,抗战初期正面战场的防御作战是有历史意义的。其一,它打击了敌人的气焰,振奋了民族精神,从而比较顺利地实现了全国性的抗日高潮。战争初期,日本帝国主义曾大肆宣传中国“不堪一击”,幻想三个月就可以灭亡中国。但是,战端一开,中国不仅没有迅速地灭亡或屈服,相反却加强了抗战到底的民族意志,使日军速战速决的计划彻底破产。在这一时期,国民党不但调集了自己的200万军队参加抗战,成为防御作战的主要力量,而且在政治上也进行了一些有限度的改革,承认了中共及其他抗日党派的合法地位,修改了一些反动法令,公布了《抗战建国纲领》,成立了咨询性的国民参政佘等等。国民党作为一个执政的党,在军事上和政治上采取了这些抗战的措施,是有利于统一全国抗战的力量。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时期的国民党政府是起了国防政府的作用。毛泽东曾指出:“抗战以来,把国内各个互相对立的阶级、党派、集团都团结起来了,各个不同的区域,不同的军队,都统一于国民政府与军事委员会指挥之下了,抗战十五个月的坚持,没有这个统一团结是不可能的。”正因为这样,使抗战初期比较顺利地出现了全国军民抗日的高潮和蓬勃向上的新气象。其二,争取了十五个月时间,为实现持久抗战创造了条件。这一时期虽然丧失了大片国土,但也给敌人在军事上和经济上造成了严重困难,迫使它不得不停止战略性的进攻。这就使我赢得了时间,保障了我国政治机构和军队主力逐渐西移,也使一部分经济和文化设施能够由沿海迁往内地,从而有可能在大西南和西北建立新的战略基地,使持久抗战得以实现。同时应该指出,国民党军队的正面防御,在客观上也掩护了八路军在华北敌后就位,减轻了敌人对我们的压力,为敌后战场的开辟创造了一定的条件。当然,八路军、新四军向敌后的挺进和敌后战场的开辟,也是对正面战场的有力支持和配合,因为“这种挺进是在敌人战略进攻阶段上我方的反进攻”。它阻止敌人继续长驱向西南、西北进攻,促使相持阶段的到来。
另一方面,在战略防御阶段丧失若干土地虽是不可避免的,但正面战场丧师失地如此之快,之多,却是国民党主观指导上的失误造成的。敌强我弱是中日战争中的一个特点,但不是惟一的特点。从敌人方面说,它还有许多弱点可资我们利用;从我们方面说,也还有许多优点可以发挥。仅就军事力量看,抗战开始时,国民党军队共有291个师另52个旅,近200万兵力,日本现役兵员仅38万,虽然中国的海空军力量劣于日军,但在南北战场上国民党军队在兵力上都占有优势。日军在装备上虽占有优势,但其在战略和战役指导上也是有懈可击的。毛泽东在总结抗战以来的经验时曾指出日军在指导上的五大错误:逐渐增加兵力,没有主攻方向,没有战略协同,失去战略时机,包围多歼灭少。这些“表现其指挥的笨拙”,因而使我有用自己聪明而有效的动作,在有组织的民众掩护之下,造成敌人错觉,调动敌人就我范围的可能性。但是,敌之弱点与我之优点,国民党都没能很好地加以利用和发挥,以至一退再退,使敌长驱直入。究其原因,是国民党在政略和战略指导上的错误,这表现了国民党在抗战中的局限性。关于这个问题,拟在后面一并分析。
二
日军占领武汉、广州后,随着战局的扩大和战线的延长,使其兵力不足、资源匮乏、财政困难的弱点日益显露。中日战争趋向长期化。日本决策者也不能不承认其迅速亡华计划的破产,认为“解决中国事件并非如此简单,国民政府现拥有240师,其外尚有游击队100万以上。如何解决此巨额之军队,如何对付国内之经济问题,及如何应付第三国之态度,均为棘手之问题。因此欲求得彻底解决中国事件则至少需时五年至十年之久”。这时,日军统帅部确定以“确保占领区”为今后主要任务,并划定由包头经黄河下流、黄泛区、庐州、芜湖、杭州一线以东为治安区,以足够兵力恢复这一区域的治安,而作战地区则限定在安庆、信阳、岳州,南昌之间的狭窄区域内,强调“今后在无特别需要,不再扩大占领区”。这样,日军基本上停止了对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抗日战争进入了战略相持阶段。
这时,日本侵略者为了摆脱长期陷于战略被动的态势,及早结束在中国的战争,对国民党采取了以军事打击和政治诱降兼施并用的方针。1938年11月3日和12月22日,日本政府的近卫首相连续两次发表声明,阐述所谓调整日中关系的新方针,改变了1月16日第一次近卫声明中关于“不以国民政府为(谈判)对手”的方针。1939年9月日在南京成立了以西尾寿造大将为总司令的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而西尾来华的一个重要使命即是“解决事变第一,作战第二”。
对于这一时期国民党的抗战及其政策也要作全面的具体的分析。应该指出,日本政府策略上的变化和这时英美策划的“东方慕尼黑”活动,很快在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得到了反映。1938年12月,亲日派的汪精卫集团公开投敌叛国,1940年3月又在南京成立了全国性汉奸政权。英美派的蒋介石集团则开始了其政策上的变化,逐渐将其重点由抗日转移到反共反人民。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就是这个转变的重要标志。在五中全会上,第一,它虽仍申言抗战到底,以期获得最后胜利与建国之成功,但又把“抗战到底”的含义解释为“恢复七七事变以前的原状”;第二、它虽然仍提出继续联共抗日,但又通过了“防共、限共、溶共”的方针。这表明国民党的妥协和反共倾向有了增长,这和抗战初期的情况相比较,确是后退了。
但是,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虽然开始出现消极避战,保存实力的意图,但仍然在支撑着正面战场,维持持久战的局面。1938年11月蒋介石在湖南南岳主持的军事会议,改变了过去所谓三期抗战的提法,认为武汉失守后中国抗战进入第二期,提出第二期抗战要政治重于军事,民众重于士兵,精神重于物质,游击战重于正规战;决定以三分之一部队配备在敌后担任游击,三分之一部队在前方抗战,三分之一到后方整训;调整了指挥系统,重新划分了战区,全国划分为包括苏鲁、冀察两个游击战区在内的共十个战区。虽然进入敌后的部队后来主要是用来对付共产党的,但这次会议的部署基本上完成了由战略防御到战略相持的转变。这时中国抗战出现了以共产党为领导的华北敌后战场和以国民党政府为主体的华中、华南正面战场,两个战场虽然在作战指导和战役上是各自进行的,但在战略总体上仍然是互相配合和互为条件的。
从武汉失守到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期间,日军对国民党战场发动了几次规模不等的战役性进攻,这些攻击不是以攻城掠地为主要目标,而是以摧毁中国继续抗战的力量,掠夺战争资源,控制交通线等为主,企图通过军事压力,迫使中国屈服。在这期间,1939年进行了海南岛、南昌、随枣、桂南和第一次长沙战役,1940年进行了枣宜战役,1941年进行了豫南、晋南、上高和第二次长沙战役。日军虽然在南昌、枣宜、豫南等战役中取得一些胜利,但由于日军已无力进行大规模的战略性进攻,因而战局没有大的变化,双方基本上保持着相对固定的作战线。
在这期间国民党军队仍表现了一定的作战能力,并取得了一些战役的胜利。如第一次长沙会战,前后近一个月,毙伤敌2万多人,迫使敌退到原来阵地;又如上高战役,原来敌决定在其主力三十三师团等部调往华北之前,对南昌方面的国民党第九战区部队发动一次进攻,结果遭到中国军队的痛击,伤亡两万多人,北调计划被打乱。此外,1939年11月至1940年3月,国民党军队还进行了一次较大规模的“冬季攻势”。这次攻势作战,在华南、敌曾在11月间占领南宁,攻陷战略要地昆仑关。12月下旬,国民党军队在白崇禧统一指挥下,向昆仑关发起反攻,经过激战,毙敌中村旅团长以下4000余人,于12月31日收复昆仑关。在华中,国民党军队以七八十个师的兵力进行攻势作战,历时40多天,给敌以一定的打击。在华北,傅作义部曾于1939年12月一度攻入包头,次年2月收复五原。这次“冬季攻势”是正面战场惟一的一次大规模反攻作战,它对于打击敌人,坚持抗战起了积极的作用。但它取得的实际战果不大。这次攻势作战曾使日军不得不重新估计中国抗战的力量,据日本防卫厅研究所战史室编《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记载,它承认“深感敌尚强大”,“证实敌人仍有二百万兵力”。但又说在如此大规模的攻势中,它没有克复任何要地,而且蒙受了极大的打击。从此以后国民党军没有进行过这种大规模的攻势作战。
应该指出,这时国民党实行的消极避战、积极反共的政策也严重影响和削弱了国民党军队的战斗力。例如1941年1月的豫南战役,日军就是利用国民党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之机进行的。1月上旬,华中日军得悉汤恩伯第三十三集团军正在东进,当时汤部位于信阳以东的遂平至项城一带,于是判断其东进目的在于进攻安徽的新四军,认为这是歼灭汤部主力的极好时机。敌迅速调动三个师团兵力分三部向豫南进犯。战役从1月下旬开始,半个多月时间,敌攻占确山、遂平、南阳、汝南、上蔡,项城等十余县城,汤部损失严重。又如,1941年日本中国派遣军根据其大本营《对支那长期作战指导计划》,确定以“加强占领区的治安”作为本年度的一个主要目标,华北日军为改善山西“治安”,决定发动晋南战役(中条山战役),以击破卫立煌的第一战区主力。5月间,日军集中六个师团又三个旅兵力向晋南等地进攻。国民党在这里有20多个师的兵力,虽然守卫部队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像师长王竣、寸性奇等都壮烈殉国,但由于消极避战方针的影响,部队很快渡过黄河,全部退出了中条山地区。在20多天作战中,部队损失惨重。据日本方面的统计,国民党军队死亡约42000人,被俘约35000人。
从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中国人民的抗战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是抗日战争发展的一个新时期。
1941年12月8日,日本偷袭美国在太平洋最大的海军基地珍珠港,同时进攻英、美、荷等国在西南太平洋的属地。太平洋战争发生后,虽然英美等国在开始时陷于十分被动的局面,但总的形势是对中国抗战有利的。这是因为,由此正式形成了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以1942年1月1日由中苏美英等26国联合签署发布的《联合国家共同宣言》为标志),中国人民抗战事业得到更多更广泛的国际同情和援助;同时太平洋战争爆发也宣告了西方帝国主义绥靖政策的彻底破产,美国为重新取得太平洋的优势,也要仰赖于中国战场,因而从这时起美国对中国的军事和经济援助大大增加,这一时期罗斯福给蒋介石的信件也不乏友好和恭维之词。1942年1月,在美英两国的建议下,设立了中国战区统帅部(含中国、泰国、越南和缅甸北部),蒋介石为统帅,史迪威为参谋长,统一指挥这一地区联合作战。美国的参战和“美援”的增加,对于一贯依赖英美的国民党是一个很大的鼓舞,也进一步坚定了蒋介石集团的抗战决心。
从这时起,中国抗战不仅在战略上配合和援助了太平洋战争,并且也在战役上支援和参加了英美军队在南方的作战。
珍珠港事件后不久,日军为配合其在东南亚地区的进攻,防止中国军队南移,集中2万兵力发起第三次长沙战役。国民党军队先后有14个军参加会战,给敌以重大杀伤。战斗持续23个昼夜,据国民党方面统计,此役毙伤敌56000人。长沙会战胜利在国内外产生很大影响,美国海军部长诺克斯发表告中国人民书称“这是所有同盟国家的胜利”。
为配合英美盟军,国民党政府还派远征军入缅作战。1942年初,日军准备攻占缅甸。应驻緬英军司令韦维尔要求,国民党政府先派空军志愿军赴仰光协防(未到,仰光已陷),后又派由三个军组成的中国远征军援緬。入缅作战的目的是配合英军,保卫滇缅路,维持我国的对外交通线。10万远征军在异国顽强抗击日军,掩护英军撤退。历时12天的同古一战,毙敌5000,伤无数。日军大佐横田日记称“南进以来,从未遭受若是之劲敌,劲敌为谁,即支那军也”。但作战后期,由于盟军指挥协同失当等原因,远征军作战遭到失败。5月,远征军一部退入印度,大部回到国内。师长戴安澜和数万壮士战死他国战场。1943年4月,退回云南的远征军与增派的部队组编为滇西远征军,撤退到印度的远征军同国内新派去的部队改编为中国驻印军。10月,中国驻印军五个师从印度进入缅甸北部,同日军展开反攻作战。1944年5月,滇西远征军17个师越过怒江,向西进攻,翌年1月在畹町与中国驻印军会师,打通了中印公路。在缅北作战中,中国军队收复大小城镇50多处,歼灭日军31000多人,为收复缅甸,配合盟军作战作出了贡献。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作战的指导中心逐渐移向南方对英美的战争,但中国仍是其所谓“大东亚圣战”的重要战场,用于中国战场的兵力仍在60万左右(如1943年侵华兵力比其在南方作战兵力约多出一倍)。这时候侵华日军仍以确保其占领区为主要任务,对国民党正面战场的军事行动则主要以太平洋战争的战略需要为转移。1942年4月,美机从太平洋上的航空母舰起飞,首次轰炸日本本土东京、神户等地,引起其国内一片惊慌。美机返航至中国浙江境内降落。这时中国沿海的一些机场确成为美国保持空军优势的重要基地。日本大本营为使其国内免受空中威胁,确保太平洋战争的顺利进行,遂命侵华日军以打通浙赣铁路、破坏沿途机场为目的,发动浙赣战役。从5月开始,日军以10万之众发动进攻,国民党军队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抵抗,给敌以相当的杀伤,但由于某些高级将领消极避战、保存实力思想严重,指挥失当,至7月,敌先后占领了48座县城,打通了浙赣路,并彻底破坏了玉山、衢州、丽水等机场及附属设施。日军大本营认为作战“目的已达”,遂按照不扩大占领区的方针,下令除确保金华及附近的地区外,恢复原态势。是役,中国军民伤亡约达25万人。这是日军为配合太平洋作战(正是日军准备进攻中途岛之际)向中国正面战场发动的一次进攻。
从1942年下半年开始,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这年6月,美国海军在中途岛海战中,重创日海军联合舰队;8月,美军攻占日军在南太平洋上具有重要战略价值的瓜达尔卡纳尔岛,从此盟军在太平洋战场逐渐转入了战略反攻。这时日本为摆脱困境,企图收缩战线,尽快结束中国战争,以便集中对付太平洋战争。它在政治上加强了所谓“招抚”政策,一面利用国民党内部派系矛盾,分化、拉拢军政要员,一面对蒋介石作出让步,以同意恢复七七事变前的状态为诱饵,要蒋政府与英美断绝关系。同时在军事上继续施加压力,企图进一步控制长江上游及洞庭湖主要产粮区,进而对重庆造成威胁之势。日本的“招抚”谋略曾收到一定的效果,国民党重要将领如吴化文、孙殿英、庞炳勋等都是在这时投敌的。但由于这时国际形势已发生重大变化,蒋介石对日和谈已表现冷淡,因而日本企图尽快结束中国战争,以便用侵华兵力去挽救太平洋战场的颓势,是根本不能实现的。至于1943年日军对正面战场发动的鄂西战役和常德战役,也没能够取得新的进展,双方仍基本上保持了原来的态势。
但是,随着太平洋战争的胜利发展,蒋介石集团依赖美英保存实力,坐等胜利的思想更加严重,抗战后期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和反共反人民政策,不仅严重削弱了中国抗战的力量,而且也使它的大批部队丧失了战斗力。1944年国民党军队在豫湘桂战役中的大溃败,就是国民党推行对日消极避战和积极反共政策的结果。
1944年,美军采取越岛进攻战术。7月占领塞班岛,把战争推进到离日本本土只有二千公里的海域。日本东京内阁被迫总辞职。日本为了扭转其在太平洋战场的不利战局,决定对中国正面战场发动一次战略性进攻,目的是要打通平汉铁路南段、粤汉铁路和湘桂铁路,开拓一条由朝鲜、中国东北,贯通华北、华中、华南直至越南的大陆交通线,以挽救孤悬南洋的日军,并摧毁美国在中国的空军基地。为此,日军作了周密的准备,大力扩编军、师团,补充兵员,并从国内和关东军抽调部队参战,整个战役先后投入了五个军十六个师团和若干旅团,总兵力达四五十万人。在越南和缅甸的日军也采取了相应的行动。日军大本营把这次豫湘桂战役称作“打通大陆交通作战”,代号为“一号作战”。整个作战从1944年4月中旬至12月下旬,包括河南战役和湘桂战役。这次虽然是日本侵华战争以来最大的一次攻势,但从总的看,日军已丧失了战略主动权,整个战局对我有利,在整个作战中国民党军队先后投入100多万兵力,占有优势,且在战役前后,敌后八路军都进行了积极的配合,这同抗战初期的形势已大不相同。但是,国民党长期执行的避战、反共政策,却使它的部队丧失了战斗力。如担任河南正面防御和黄河河防的第一战区副总司令汤恩伯(总司令蒋鼎文)所部30余万人,经营河南数年,以反共、扰民为能事,结果在日军10余万兵力的进攻下,除非嫡系部队(如孙蔚如、马法五、刘茂恩等部)进行一些比较认真的抵抗外,而号称精锐的汤恩伯部队却一触即溃。河南战役前后38天丢失城市38座,折兵过半。在湘桂战役中,主要进行了衡阳保卫战,从6月22日至8月7日,坚守危城47天,连续打破日军两次总攻击,打得顽强、出色,但最后却以守城指挥第十军军长方先觉叛国投敌而告终。在豫湘桂战役的短短八个月中,日军长驱直入,从河南一直打到广西,并继续沿黔桂线推进到贵州独山一带,直逼重庆。国民党军队损失兵力六七十万,丢失包括146座大中城市的20万平方公里土地,7个空军基地和36个飞机场,使6000多万同胞沦于敌人的铁蹄之下。应该指出,日军虽然打通了平汉、粵汉和湘桂铁路,但因运输材料缺乏,大陆交通线始终未能全线通车,它的战略意图实际上未能实现。相反,由于战线的延长,分散和牵制了大量日军,使这次战役不但不能挽救其日趋恶化的总态势,却给中国抗日军民的反攻造成了有利时机。
总之,相持阶段到来以后,国民党抗战的消极方面开始突出,特别是抗战后期它的危害作用更加明显。但是,由于国际和国内各种因素的制约,这时的国民党统治集团仍然是具有既抗日又妥协,既抗战又消极避战,既联共又反共这样两面性的。在战略相持阶段,国民党军队进行了18次会战,并两度赴缅作战,仍牵制了约占40%左右的侵华日军,维持了持久抗战的局面。在整个八年抗战中,据国民党政府公布的材料,共作战4万多次,其中会战22次,重要战斗1170次,毙伤日军237万。因此,仅就抗战而言,国民党的积极作用是其基本的方面,是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三
七七事变后,国民党接受了中共倡导的团结抗战的主张,这是国民党历史发展中的一个进步,基合乎民族大义的行动。“当时全国人民,我们共产党人,其他民主党派,都对国民党政府寄予极大的希望,就是说,希望它乘此民族艰危、人心振奋的时机,厉行民主改革,将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三民主义付诸实施。”抗战一开始,中共就制定了国共两党长期合作的方针,希望国民党彻底改变十年内战时期的错误政策,以实现共同抗日与共同建国的目的。
如前所述,国民党在八年抗战中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它并没有如全国人民所希望的,彻底弃旧图新,相反却重蹈过去的一套错误做法,这不仅限制了它在民族战争中应有作用的发挥,削弱了全国军民的抗战力量,并且成为最终导致国共两党关系破裂,使它自己丧失人心的深刻原因。这恰恰表现了它作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政党在民族战争中的阶级局限性。这种阶级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表现在政治上它执行一条反人民的片面抗战路线。抗战初期毛泽东就指出:当时“参战的地域虽然是全国性的,参战的成分却不是全国性的。广大的人民群众依然如过去一样被政府限制着不许起来参战,因此现在的战争还不是群众性的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战争而不带群众性,是决然不能胜利的。”因而,关于如何抗战问题,即全面抗战还是片面抗战,成为抗战时期国共两党争论的主要问题,也是关系到抗战前途的根本问题。应该看到,国民党中的多数人是具有爱国的民族意识,是有抗战的热情和决心的,但它的统治集团则主要是从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出发,被迫参加和坚持抗战的,它的抗日是具有不彻底性和妥协性的。国民党蒋介石集团虽然在抗战初期有条件地承认了人民的某些民主权利,但由于它畏惧人民力量的壮大,基本上是把解决中国抗战问题的希望寄托在英美等国身上,因而不愿利用和发挥民族解放战争中的有利条件,拒绝中共和其他民主党派关于实行全面的全民族抗战的主张,力图把抗日战争局限于单纯的政府和军队抗战。这是国民党丧师失地的深刻的政治原因。
相持阶段到来后,由于中共领导的人民抗日力量迅速壮大,在华北和华中开辟了广大的敌后根据地;由于日本基本停止了对正面战场的战略性进攻,对国民党更多地采用政治诱降的策略;由于国民党已将其主力转移到西南后方,又有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畏惧和仇视人民力量的情绪迅速增长,逐渐把注意力从日本帝国主义身上移到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身上来。这时国民党采取了对日消极作战、对内积极反共的政策,它不但“将抗日初期人民和各抗日党派争取得来的某些权利,一概取消”。而且还不断制造反共的军事磨擦。据统计,从1938年10月至1944年3月,六年多的时间,国民党使用约190万军队,制造反共磨擦事件约2500多次,其中并有三次反共高潮。武汉失守后国民党曾决定抽调三分之一兵力到敌后开展游击战争,这个决定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是,进入敌后的部队却主要被用来对付共产党,特别是1941年以后,蒋介石采取罪恶的“曲线救国”政策,指使敌后部队投降敌方,以伪军旗号进攻解放区。据统计,进入华北,华中敌后的国民党军队不下100万(1941年在华北约有80万,华中约有20万),除被敌人消灭或撤回后方夕卜,投敌的竟达50万人(占伪军总数62%),到1944年留在华北敌后的不过二三万人。这样,不仅严重削弱了抗战力量,而且正是由于国民党坚持一党专政及其错误的政策,导致了它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严重困难,日渐失去了民心。
其次,在军事上采用消极防御战略并沿袭腐败的军事制度。在敌强我弱的军事形势下,我们作战的基本方针应采取“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以运动战为主,以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为主要目的。而国民党军队的战略防御,始终把阵地防御战放在主要地位,企图以单纯防御阻止敌人的进攻。这种消极防御的方针,即不积极寻找和利用有利战机灵活机动地打击敌人有生力量,不敢把主力用于侧面,采取迂回包围的战法,调动和分散敌人,达到各个歼敌的目的,而是在预定的阵地上摆出决战架势,等待敌人进攻,在固定的地域与敌人拼消耗。这就置自己于被动地位,既不能为进攻战役和战略反攻创造条件,又使敌人的长处得到发挥。八年抗战中正面战场22次大的会战,绝大多数都是这种阵地防御战。正是“这种笨拙的战略,就使得前线将士英勇的奋斗不能获得应有的战果”。
国民党军队在作战指挥上的错误,还和它腐败的军事制度紧密相关。国民党军队内部派系复杂,上下争权夺利,互相排挤倾轧,在战场上各自保存实力,互不配合。国民党军事上实际是军事寡头制度,在战略和战役指挥上,蒋介石独揽军权,一切由个人说了算,使正确意见得不到采纳。他甚至进行越级指挥,各级指挥官形同虚设。一些高级指挥官患有严重的恐日病,腐朽无能,敌未至而自溃和临阵逃脱的丑行并不鲜见。这连蒋介石也不得不承认,他曾说无论在上海或其他战场,每次后退,都是我们高级将领,判断敌情不明,乃至贪生怕死,不敢指挥部队,先自脱逃所以不能掌握部队,如此,你当主官的先违犯军纪,犯了临阵脱逃之罪,叫部下如何不溃散,不犯罪呢?这是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国民党战场一个方面的情况。所以,毛泽东曾指出:“现在国民党军队的制度还是老制度,要用这种制度的军队去战胜日本帝国主义是不可能的。”“广大的将士虽有忠勇之心,但束缚于旧制度,无法发挥其积极性。”
再者,在对日态度上表现为既抗日又妥协动摇。抗战八年,国民党政府始终不敢依靠和发动人民抗战,最初它把制止日本侵略的希望寄托在英美苏各国的干涉上,随后又间接或直接地同日本秘密谈判,进行“和平”运动。它是一面抗战,一面又是随时准备妥协。1937年12月,国民党政府就响应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的“和平”调停;1938年国民党政府外交部主管对日事务官员董道宁、高宗武奉命秘密赴日,沟通“和平”渠道;1939年3月和6月日蒋代表先后在香港、澳门秘密会谈,并曾达成举行板桓征四郎、蒋介石长沙会谈的协议;1940年至1941年,日本又通过司徒雷登(燕京大学校长)奔走于北平、重庆之间,进行“和平”搭线;1944年,日本通过释放吴开先(曾任国民党中组部副部长、上海市社会局局长),再次向重庆试探;直到1945年7月,当日本败局已定时,仍有日军代表与国民党高级将领在河南新站集的密谈。
总之,国民党在八年抗战中,做了许多错事和坏事,而对内反共反人,民和对日妥协动摇,则集中表现了它作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政党的阶级局限性。国民党在抗战中后期曾积极地进行反共活动,但终未酿成全面内战,曾多次谋求对日妥协,但也未成为事实。这从根本上说,是因为中日民族矛盾始终是主要矛盾,日本的侵略活动和它对国民党的苛刻的“和平”条件,既损害英美的在华利益,也威胁着国民党的统治,这就不能不对国民党的反共和妥协活动起着制约的作用;同时,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的反动方面采取了正确的斗争策略,妥善地处理了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关系,既使人民抗日力量在斗争中得到了发展,又限制了国民党的反共和妥协的企图,从而维护了国共合作的局面。
抗战八年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坚持抗战、团结、进步,是争取这场民族解放战争胜利的要求,是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愿望,国民党在这方面曾做过一些利国利民的好事,因而得到人民群众的一定的谅解和拥护。但是,国民党统治集团并没有把它贯彻到底,而是采取错误的政策,违背了历史发展的要求和人民的根本愿望,从而使自己走向了反面,这对国民党来说不能不是一个重要的教训。
历史经验还告诉我们,国共两党是中国的两大政党,两党合作有利于国家民族。毛泽东曾多次热情地评价国共合作的意义,他说:“中国军队在民族公敌面前,互相忘记了旧怨,而变为互相援助的亲密的朋友,这是中国绝不会亡的基础。”第二次国共合作取得的抗日战争的辉煌胜利和随后发生的历史曲折,证明了“联共则荣,反共则衰”的真理,这对今天仍然是十分有益的历史经验。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论文集》,1985)
看过本书的人还看过
-
文学小说 【已完结】
文君和韦晓晴成为情人时,并不知道马萍早已和别的男人好上了。其实马萍和别的男人好上这半年多的时间里,马萍从生理到心理是有一系列变化的,只因文君没有感觉到,如果在平时,文君是能感觉到的,因为文君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