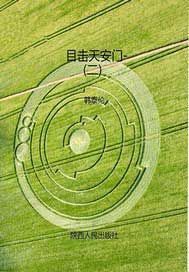第51章“两个凡是”定基调真理讨论大展开(6)
初稿第一段中曾有这样几句:“同志们反映,这是又一次思想解放运动,我们认为,这次讨论不仅有利于弄清马克思主义的这个基本观点,而且,关系到我们党的整个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关系到我国革命前途的大问题,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熊复说,汪东兴认为这样讲估计太高了,不是什么关系国家命运前途的大事,只能说是有利于开展百家争鸣,活跃思想。于是,这几句话就改为:“出现了敞开思想,勇于争鸣的新气象。我们认为,通过这次重温毛主席的《实践论》,弄清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以利于在政治思想领域里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具有重大意义。”
这就是第三稿,也叫9月19日未定稿。
这个稿子,曾以《红旗》杂志社党委的名义于9月20日送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征求意见,哲学研究所经部分人阅读和座谈,于24日提出六条意见退给《红旗》杂志社党委。
由于哲学研究所的六条意见既尖锐又中肯,加之当时各方面对《红旗》杂志意见纷纷,因此,此文一直没能刊用出去。后来,到了11月份,又修改一次,删去五、六两节,只留下前四节,准备作为纪念毛泽东八十五周年诞辰的文章,在第十二期发表,列入选题计划,这就是12月9日的修改稿。因为真理标准讨论的深入和明朗化,《红旗》已完全陷入被动,此文终于流产。
这篇文章虽未发表,却由此而引发了理论务虚会的召开。9月下旬,《红旗》杂志社收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对《重温〈实践论〉》一文的意见后,就将此文及哲学所的意见上报中央政治局常委。叶剑英看后,提议中央召开一次理论工作务虚会,大家把不同意见摆出来,在充分民主讨论的基础上,统一认识,把这个问题解决一下。――这就是1979年年初那个有名的理论务虚会的来历。
谭震林文章被阻发表
在熊复炮制《重温〈实践论〉》的同时,《红旗》又发生了一件引人注目的事件,这就是阻止谭震林文章的发表。
1978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诞辰八十五周年纪念日,12月出版的第十二期《红旗》自然要有纪念文章,8月份编辑部就积极筹划,约请谭震林写一篇回忆毛泽东当年领导井冈山斗争的文章。
谭震林在“文革”中曾因抵制林彪、江青的作乱,被打成“二月逆流”的黑干将,后又被诬陷为“叛徒”,长期遭受摧残。《红旗》编辑部派人向他约稿时,他斩钉截铁地说,写文章不能只讲历史,要从现实着眼,要我写文章,我就要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说明毛泽东思想是从实践中来,又经过革命实践检验的科学真理。
10月下旬,谭震林文章的初稿送到《红旗》编辑部,熊复看后,认为文章第四部分讲的都是有关真理标准的问题,应删掉。责任编辑认为,文章是谭震林写的,以个人名义发表,要尊重作者的意见,不能强加于人,不能删。
有意思的是,这边的争执还未定局,谭震林又送来了新的修改稿,把第四部分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进一步加强,并且,给《红旗》编辑部写信说:“文章只作了一点小的修改,主要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这一点原文上是有的,只是不够突出,不够明确,我把它加强了。”“如果你们认为还有什么修改,请想好后,到我家来,当面商量。”
熊复看了谭震林的信和改稿哭笑不得,但仍坚持要删去文中有关阐明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那一部分,并且,写了一个条子,讲了两点处理意见:一、派人去同他谈,说明中央给《红旗》的方针是不介入讨论,请他考虑删去有关段落。二、如谭震林不同意删,就照他的意见印出,送中央常委审查。
11月14日,编辑部派人去见谭震林,转述了熊复的意见。谭震林当即鲜明地表示,文章中的材料可以动,观点不能动。实践标准的讨论是全党的大事。告诉熊复,这样做丢不了党籍,住不了牛棚。有谁来辩论,找我好了。对这篇文章我想了两个月,想出了两句话:凡是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就要坚持;凡是实践证明是错误的,就要改正。
熊复拗不过谭震林,在无可奈何之中,于11月16日将谭文送审,并给汪东兴写一报告:
汪副主席并华主席:
我们请谭震林同志写了一篇纪念毛主席诞辰85周年的文章,准备在十二期发表。谭震林同志强调要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作为这篇文章的指导思想,这就是使《红旗》卷入这场讨论。我们建议他修改,他表示不同意,就要请中央主席审查。现送上这篇文章,请审定。
华国锋、邓小平、李先念看后,同意《红旗》发表谭文。邓小平、李先念还写了批语。邓小平写道:“我看这篇文章好,至少没有错误。改了一点,如《红旗》不愿登,可转《人民日报》登。为什么《红旗》不卷入?应该卷入,可以发表不同观点的文章。看来不卷入本身,可能就是卷入。”李先念在19日写的批语是:“文章确长,没有时间看,反映对《红旗》意见不少。”21日,他看了这篇文章,又写道:“我看了这篇文章,谭震林同志讲的是历史事实,应当登,不登《红旗》太被动了,《红旗》已经很被动了。”
接到这些批语后,熊复依然不敢做主,又跑到汪东兴那里问怎么办。汪东兴也无可奈何,只好说,那只好这样。至此,谭震林的文章送新华印刷厂发排,于十二期刊出。
在此期间,熊复所唱的一系列“反调”,并不代表《红旗》的编辑们。《重温〈实践论〉》那篇文章,照理是编辑部哲史组的事,但文章的起草、修改均未让哲史组的编辑们插手。对《红旗》所发生的一些不正常的现象,一些人蒙在鼓里,洞观的人则憋着一肚子火。随着形势的发展,《红旗》愈来愈被动,这股火也越憋越大,然而,只能“在地下运行”。半年后,终于冲破地表,喷焰而出了。1978年11月23日,在《红旗》杂志院内,王忠明、邢雁二人贴出一张大字报,提出对《红旗》杂志当前一些问题的看法,要求迅速改变《红旗》的面貌,立即在社内外引起轰动,《红旗》的人也感到舒心。
大字报有关真理标准讨论问题是这样说的:作为党中央理论刊物的《红旗》杂志,理所当然的要大力参加讨论。但是,《红旗》杂志至今没有发表过一篇文章,保持沉默。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我们从熊复同志对这个问题的态度可以找到答案。熊复同志不止一次地表白,他并不反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没发表过文章,也没有作过讲谈。事实并不如此。他刚来《红旗》不久,就在一次会上针对《光明日报》发表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说:“我有不同意见,在这里表明我自己的观点,这些文章有问题。”最近,熊复在召集一些同志座谈宣传问题的会上,有的同志提到《红旗》没有刊登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很被动,熊复激动地说:“你被动什么,我并不感到被动”,“这没有什么关系,不要怕这种人”,“有人跳得很高,其实,他作了些什么,中央很清楚,我今天不点他的名。”我们要问熊复同志,这难道不是反对吗?
熊复同志还表白说,他授意一位同志写过文章,我们看看写的这篇《重温〈实践论〉》是一篇什么样文章呢?这篇文章全文两万多字,除了教科书式的毫不联系实际地讲了理论和实践的关系外,很大篇幅反驳所谓“怀疑论”“不可知论”和“海外奇谈”,这种文章实质上跟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唱反调。
大字报贴出后的第三天,即11月25日,熊复在大字报旁边贴了一张小字报:
读了王忠明、邢雁同志的大字报,我非常高兴,为这张大字报欢呼。
王、邢两同志对我的工作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总的来说,《红旗》的运动和工作落后于当前的形势,究其因由,与我的领导思想和工作作风分不开,我要负全部的责任。我认为,这样的批评中肯。我诚恳地接受王、邢二同志的批评。可见王、邢二同志的批评是善意的。因为,他们提出问题来,要迅速改变《红旗》的落后面貌,紧紧跟上新长征的步伐。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尚未解决的大问题。
至于我,从王、邢两位同志的大字报得到很大的启发。我这个人的缺点很多,几个月来,这样那样的错误也是有的。大家都知道,我现在还来不及总结我在这个时期的工作,在适当的时候,应该作出总结,汲取教训。错了就改,我决心改正工作中的错误。希望同志们在这方面帮助我,督促我,教我!
熊复
1978年11月25日
汪东兴批评《中国青年》
粉碎“四人帮”后,一些在“文革”中被迫停刊的报纸、杂志陆续复刊。“文革”前,在青年中有广泛影响的《中国青年》杂志,拟定于1978年9月复刊。在这之前,成立了共青团“十大”筹备委员会,着手召开共青团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新的团中央委员,恢复在“文革”中被“砸掉”的团的中央机构,开展正常的团的工作,《中国青年》的复刊工作置于团“十大”筹委会的领导之下,而汪东兴又是中央分管工、青、妇工作的,团“十大”筹委会当然由他来直接联系和领导。
复刊后的第一期《中国青年》定于9月11日出版。
9月10日,北京承印的60万份《中国青年》第一期已全部印完,全国其它7个代印点也大部分印完。在北京地区,已有4万多份通过邮局送到读者手里。这一期介绍《革命何须怕断头》,介绍了青年工人韩志雄的事迹,1976年4月5日“天安门事件”,他同“四人帮”作斗争,在迫害面前坚强不屈,还选登童怀周编辑的《天安门诗抄》(这本诗集曾印行过,遭到汪东兴批评,此次,《中国青年》以“青年革命诗抄”为栏题,选登其中一小部分)。在群众迫切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同时,《中国青年》推出这样的文章,自然受到了读者欢迎,争相阅读。
不料,10日下午,共青团“十大”筹委会负责人韩英接到汪东兴的一个电话。汪提出了四点意见:
(1)《中国青年》第一期为什么只有叶副主席题词,没有华主席题词;
(2)《革命何须怕断头》所宣传的韩志雄,你们了解清楚了吗?这个人有问题;
(3)童怀周的《天安门诗抄》怎么又出来了;
(4)没有纪念毛主席逝世两周年的文章。
当时,韩英即将上述意见传达给《中国青年》编辑部,并宣布刊物停印停发,等待研究处理。
编辑部当即认真研究,感到这四条意见并没有什么道理。
思来想去,编辑部的同志认定在编发这一期刊物的过程,并无处置不当之处,对汪东兴的四点批评难以接受。
9月11日,编辑部将自己的看法写信报告华国锋及其他几位中央副主席,并且,同时报给了团“十大”筹委会。
9月12日晚上,韩英找杂志社组长以上干部开会,传达他同汪东兴商定的对这期刊物的四点处理意见:
(1)由汪东兴去请华国锋题词(这时,华国锋出访四国)。
(2)增加毛泽东的诗词三首及照片。
(3)删去《革命何须怕断头》一文中“这场伟大壮烈的人民运动,被‘四人帮’无情地镇压下去了……”等段落。
(4)删去《青年革命诗抄》的天安门题图和编者按。
韩英还特地念了1977年3月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中,有关天安门事件和“两个凡是”的段落,说以上两篇文章同华国锋讲话的精神不符,有损毛泽东的形象。
9月13日下午,华国锋的题词送到编辑部。当晚,编辑部向团“十大”筹备会报告:华主席的题词收到了;已向外地发出电报,立即停印停发;北京印好的全部停发。可以增加华主席题词和毛主席诗词三首。但《革命何须怕断头》一文和《青年革命诗抄》以不改为好。因为,这两篇东西内容并没有错,而且,已有4万多份刊物发到了读者手中,改了以后将造成同一份刊物两个版本的局面,不但会引起读者不满,若追问起删改原因,将无言以对,不利于安定团结。遗憾的是,团“十大”筹备会没有接受编辑部的这个意见。
就在这前后,复刊第一期遇到的种种磕碰传到社会上,引起群众强烈不满。不少读者投书编辑部,更有人在西单街头贴出大字报“救救《中国青年》”。
9月14日,编辑部再次上书华国锋及几位中央副主席,表示最好不要删改《革命何须怕断头》及《青年革命诗抄》。
当天晚上,汪东兴又把杂志社组长以上干部召集到人民大会堂开会。会议在紧张的气氛中,从八点一刻开始,一直开到午夜十二点五十分。
会上,汪东兴对编辑部干部的批评,已经可以使用“申斥”这两个字眼了。
他说:“中央叫我分管工青妇,这个你们知道不知道?我翻了这期《中国青年》的大概内容,没详细看,还以为是清样,不知道已经正式出版。如正式出版,就不是要我审查了。今天把口径统一一下。你们已经发出41000份,发都发了,怎么叫审查?如果,你们认为我们没有审查任务,那我们就不审查了。”
他说:“不要我审查,我不负责,我这个人好办。你青年社通报这个情况,离开了团‘十大’筹备会。你们直接写信给中央,并没有通过筹备会转给我。不是和筹委会打官司,而是涉及到中央。天安门事件,华主席已经讲了。”
这时,他念了华国锋在1977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中关于天安门事件的“两个凡是”的段落。
他接着说:“刚才第一个是讲的组织观念。第二个讲文章内容符不符合华主席对天安门事件的估价。华主席在天安门问题上早就讲过,为什么有人还在上面纠缠?”
他说:“你叫我提意见我就提,第一期应该有毛主席的东西,应该考虑。华主席不在,叶副主席、聂帅题了字,我再给华主席讲讲,题个字嘛!毛主席逝世两周年,有总理的照片,主席的一个都没有,不考虑考虑?我说可以考虑一下。再有,我说里边有两篇文章内容与华主席讲话符合不符合,考虑考虑。再有,英雄人物不是不可以写,但是,天安门事件的性质已经定了。是你们记者写的文章,与转载不一样。”
他说:“为什么不发华主席的题词?华是毛主席的接班人,为什么不能等两天?”
他说:“一是不动了,就照你们的意见办,华主席题词也不登了。这是你们的意见。怕什么?最多只能说汪东兴讲的、韩英讲的、筹备会讲的都不灵嘛!最多说你们打了个胜仗。题词可以不登,主席诗词也不登。这一期,中央没有审查,就是中国青年社发出的,我声明,我没审查。第二条意见,把华主席题词、毛主席诗词三首和照片放进去,其他不动,因为动了也不行。我看这两个意见,不可能有第三个意见。”
他说:“历史上有教训,凡是离开党的领导,一事无成,会碰得头破血流。”
他说,“今天批评一下,说得不恰当,请你们原谅。我的心还是好的,不能说你对我错了,都对。”
总编辑火速派人赴印刷厂,为每册尚未发表的《中国青年》夹进华国锋题词、毛泽东诗词重印,又收回已发出的4万多份。
第二节 三中全会改变中国邓小平成领导核心(2)
各路“诸侯”陆续表态
真理标准的讨论,很快就从北京向四面八方辐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负责人都在严肃地思考这个问题,有的爽快了当,有的颇费踌躇;这倒并不因为这个问题在理论上有什么深奥难懂之处,关键在于“妾身未分明”――拿不准在政治上究竟采取何种态度为宜。当然,问题本身所牵连底蕴之深,所包容方面之广,也给这些在各色各样的战场上出生入死,翻上滚下的豪杰们一些为难。
在这个问题上,最先明确亮出自己的观点的是,当时的辽宁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和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杨易辰。
任仲夷在辽宁省委主办的理论月刊《理论与实践》第八、九期合刊上发表文章,题目是:
《理论上根本的拨乱反正》。
以后其他省、市、自治区的第一书记和各大军区的主要负责人,纷纷在各种会议上发表讲话,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新华社一一播发消息,首都报纸则作为要闻争相刊登。
按照新华社报道的时间,依次是:
8月27日汪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
9月10日廖志高福建省委第一书记
9月19日习仲勋广东省委第二书记
9月24日铁瑛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李本平浙江省委书记
9月27日江渭清江西省委第一书记
10月3日刘子厚河北省委第一书记
10月5日谭启龙青海省委第一书记
10月8日王铎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
这就是第三稿,也叫9月19日未定稿。
这个稿子,曾以《红旗》杂志社党委的名义于9月20日送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征求意见,哲学研究所经部分人阅读和座谈,于24日提出六条意见退给《红旗》杂志社党委。
由于哲学研究所的六条意见既尖锐又中肯,加之当时各方面对《红旗》杂志意见纷纷,因此,此文一直没能刊用出去。后来,到了11月份,又修改一次,删去五、六两节,只留下前四节,准备作为纪念毛泽东八十五周年诞辰的文章,在第十二期发表,列入选题计划,这就是12月9日的修改稿。因为真理标准讨论的深入和明朗化,《红旗》已完全陷入被动,此文终于流产。
这篇文章虽未发表,却由此而引发了理论务虚会的召开。9月下旬,《红旗》杂志社收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对《重温〈实践论〉》一文的意见后,就将此文及哲学所的意见上报中央政治局常委。叶剑英看后,提议中央召开一次理论工作务虚会,大家把不同意见摆出来,在充分民主讨论的基础上,统一认识,把这个问题解决一下。――这就是1979年年初那个有名的理论务虚会的来历。
谭震林文章被阻发表
在熊复炮制《重温〈实践论〉》的同时,《红旗》又发生了一件引人注目的事件,这就是阻止谭震林文章的发表。
1978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诞辰八十五周年纪念日,12月出版的第十二期《红旗》自然要有纪念文章,8月份编辑部就积极筹划,约请谭震林写一篇回忆毛泽东当年领导井冈山斗争的文章。
谭震林在“文革”中曾因抵制林彪、江青的作乱,被打成“二月逆流”的黑干将,后又被诬陷为“叛徒”,长期遭受摧残。《红旗》编辑部派人向他约稿时,他斩钉截铁地说,写文章不能只讲历史,要从现实着眼,要我写文章,我就要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说明毛泽东思想是从实践中来,又经过革命实践检验的科学真理。
10月下旬,谭震林文章的初稿送到《红旗》编辑部,熊复看后,认为文章第四部分讲的都是有关真理标准的问题,应删掉。责任编辑认为,文章是谭震林写的,以个人名义发表,要尊重作者的意见,不能强加于人,不能删。
有意思的是,这边的争执还未定局,谭震林又送来了新的修改稿,把第四部分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进一步加强,并且,给《红旗》编辑部写信说:“文章只作了一点小的修改,主要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这一点原文上是有的,只是不够突出,不够明确,我把它加强了。”“如果你们认为还有什么修改,请想好后,到我家来,当面商量。”
熊复看了谭震林的信和改稿哭笑不得,但仍坚持要删去文中有关阐明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那一部分,并且,写了一个条子,讲了两点处理意见:一、派人去同他谈,说明中央给《红旗》的方针是不介入讨论,请他考虑删去有关段落。二、如谭震林不同意删,就照他的意见印出,送中央常委审查。
11月14日,编辑部派人去见谭震林,转述了熊复的意见。谭震林当即鲜明地表示,文章中的材料可以动,观点不能动。实践标准的讨论是全党的大事。告诉熊复,这样做丢不了党籍,住不了牛棚。有谁来辩论,找我好了。对这篇文章我想了两个月,想出了两句话:凡是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就要坚持;凡是实践证明是错误的,就要改正。
熊复拗不过谭震林,在无可奈何之中,于11月16日将谭文送审,并给汪东兴写一报告:
汪副主席并华主席:
我们请谭震林同志写了一篇纪念毛主席诞辰85周年的文章,准备在十二期发表。谭震林同志强调要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作为这篇文章的指导思想,这就是使《红旗》卷入这场讨论。我们建议他修改,他表示不同意,就要请中央主席审查。现送上这篇文章,请审定。
华国锋、邓小平、李先念看后,同意《红旗》发表谭文。邓小平、李先念还写了批语。邓小平写道:“我看这篇文章好,至少没有错误。改了一点,如《红旗》不愿登,可转《人民日报》登。为什么《红旗》不卷入?应该卷入,可以发表不同观点的文章。看来不卷入本身,可能就是卷入。”李先念在19日写的批语是:“文章确长,没有时间看,反映对《红旗》意见不少。”21日,他看了这篇文章,又写道:“我看了这篇文章,谭震林同志讲的是历史事实,应当登,不登《红旗》太被动了,《红旗》已经很被动了。”
接到这些批语后,熊复依然不敢做主,又跑到汪东兴那里问怎么办。汪东兴也无可奈何,只好说,那只好这样。至此,谭震林的文章送新华印刷厂发排,于十二期刊出。
在此期间,熊复所唱的一系列“反调”,并不代表《红旗》的编辑们。《重温〈实践论〉》那篇文章,照理是编辑部哲史组的事,但文章的起草、修改均未让哲史组的编辑们插手。对《红旗》所发生的一些不正常的现象,一些人蒙在鼓里,洞观的人则憋着一肚子火。随着形势的发展,《红旗》愈来愈被动,这股火也越憋越大,然而,只能“在地下运行”。半年后,终于冲破地表,喷焰而出了。1978年11月23日,在《红旗》杂志院内,王忠明、邢雁二人贴出一张大字报,提出对《红旗》杂志当前一些问题的看法,要求迅速改变《红旗》的面貌,立即在社内外引起轰动,《红旗》的人也感到舒心。
大字报有关真理标准讨论问题是这样说的:作为党中央理论刊物的《红旗》杂志,理所当然的要大力参加讨论。但是,《红旗》杂志至今没有发表过一篇文章,保持沉默。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我们从熊复同志对这个问题的态度可以找到答案。熊复同志不止一次地表白,他并不反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没发表过文章,也没有作过讲谈。事实并不如此。他刚来《红旗》不久,就在一次会上针对《光明日报》发表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说:“我有不同意见,在这里表明我自己的观点,这些文章有问题。”最近,熊复在召集一些同志座谈宣传问题的会上,有的同志提到《红旗》没有刊登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很被动,熊复激动地说:“你被动什么,我并不感到被动”,“这没有什么关系,不要怕这种人”,“有人跳得很高,其实,他作了些什么,中央很清楚,我今天不点他的名。”我们要问熊复同志,这难道不是反对吗?
熊复同志还表白说,他授意一位同志写过文章,我们看看写的这篇《重温〈实践论〉》是一篇什么样文章呢?这篇文章全文两万多字,除了教科书式的毫不联系实际地讲了理论和实践的关系外,很大篇幅反驳所谓“怀疑论”“不可知论”和“海外奇谈”,这种文章实质上跟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唱反调。
大字报贴出后的第三天,即11月25日,熊复在大字报旁边贴了一张小字报:
读了王忠明、邢雁同志的大字报,我非常高兴,为这张大字报欢呼。
王、邢两同志对我的工作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总的来说,《红旗》的运动和工作落后于当前的形势,究其因由,与我的领导思想和工作作风分不开,我要负全部的责任。我认为,这样的批评中肯。我诚恳地接受王、邢二同志的批评。可见王、邢二同志的批评是善意的。因为,他们提出问题来,要迅速改变《红旗》的落后面貌,紧紧跟上新长征的步伐。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尚未解决的大问题。
至于我,从王、邢两位同志的大字报得到很大的启发。我这个人的缺点很多,几个月来,这样那样的错误也是有的。大家都知道,我现在还来不及总结我在这个时期的工作,在适当的时候,应该作出总结,汲取教训。错了就改,我决心改正工作中的错误。希望同志们在这方面帮助我,督促我,教我!
熊复
1978年11月25日
汪东兴批评《中国青年》
粉碎“四人帮”后,一些在“文革”中被迫停刊的报纸、杂志陆续复刊。“文革”前,在青年中有广泛影响的《中国青年》杂志,拟定于1978年9月复刊。在这之前,成立了共青团“十大”筹备委员会,着手召开共青团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新的团中央委员,恢复在“文革”中被“砸掉”的团的中央机构,开展正常的团的工作,《中国青年》的复刊工作置于团“十大”筹委会的领导之下,而汪东兴又是中央分管工、青、妇工作的,团“十大”筹委会当然由他来直接联系和领导。
复刊后的第一期《中国青年》定于9月11日出版。
9月10日,北京承印的60万份《中国青年》第一期已全部印完,全国其它7个代印点也大部分印完。在北京地区,已有4万多份通过邮局送到读者手里。这一期介绍《革命何须怕断头》,介绍了青年工人韩志雄的事迹,1976年4月5日“天安门事件”,他同“四人帮”作斗争,在迫害面前坚强不屈,还选登童怀周编辑的《天安门诗抄》(这本诗集曾印行过,遭到汪东兴批评,此次,《中国青年》以“青年革命诗抄”为栏题,选登其中一小部分)。在群众迫切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同时,《中国青年》推出这样的文章,自然受到了读者欢迎,争相阅读。
不料,10日下午,共青团“十大”筹委会负责人韩英接到汪东兴的一个电话。汪提出了四点意见:
(1)《中国青年》第一期为什么只有叶副主席题词,没有华主席题词;
(2)《革命何须怕断头》所宣传的韩志雄,你们了解清楚了吗?这个人有问题;
(3)童怀周的《天安门诗抄》怎么又出来了;
(4)没有纪念毛主席逝世两周年的文章。
当时,韩英即将上述意见传达给《中国青年》编辑部,并宣布刊物停印停发,等待研究处理。
编辑部当即认真研究,感到这四条意见并没有什么道理。
思来想去,编辑部的同志认定在编发这一期刊物的过程,并无处置不当之处,对汪东兴的四点批评难以接受。
9月11日,编辑部将自己的看法写信报告华国锋及其他几位中央副主席,并且,同时报给了团“十大”筹委会。
9月12日晚上,韩英找杂志社组长以上干部开会,传达他同汪东兴商定的对这期刊物的四点处理意见:
(1)由汪东兴去请华国锋题词(这时,华国锋出访四国)。
(2)增加毛泽东的诗词三首及照片。
(3)删去《革命何须怕断头》一文中“这场伟大壮烈的人民运动,被‘四人帮’无情地镇压下去了……”等段落。
(4)删去《青年革命诗抄》的天安门题图和编者按。
韩英还特地念了1977年3月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中,有关天安门事件和“两个凡是”的段落,说以上两篇文章同华国锋讲话的精神不符,有损毛泽东的形象。
9月13日下午,华国锋的题词送到编辑部。当晚,编辑部向团“十大”筹备会报告:华主席的题词收到了;已向外地发出电报,立即停印停发;北京印好的全部停发。可以增加华主席题词和毛主席诗词三首。但《革命何须怕断头》一文和《青年革命诗抄》以不改为好。因为,这两篇东西内容并没有错,而且,已有4万多份刊物发到了读者手中,改了以后将造成同一份刊物两个版本的局面,不但会引起读者不满,若追问起删改原因,将无言以对,不利于安定团结。遗憾的是,团“十大”筹备会没有接受编辑部的这个意见。
就在这前后,复刊第一期遇到的种种磕碰传到社会上,引起群众强烈不满。不少读者投书编辑部,更有人在西单街头贴出大字报“救救《中国青年》”。
9月14日,编辑部再次上书华国锋及几位中央副主席,表示最好不要删改《革命何须怕断头》及《青年革命诗抄》。
当天晚上,汪东兴又把杂志社组长以上干部召集到人民大会堂开会。会议在紧张的气氛中,从八点一刻开始,一直开到午夜十二点五十分。
会上,汪东兴对编辑部干部的批评,已经可以使用“申斥”这两个字眼了。
他说:“中央叫我分管工青妇,这个你们知道不知道?我翻了这期《中国青年》的大概内容,没详细看,还以为是清样,不知道已经正式出版。如正式出版,就不是要我审查了。今天把口径统一一下。你们已经发出41000份,发都发了,怎么叫审查?如果,你们认为我们没有审查任务,那我们就不审查了。”
他说:“不要我审查,我不负责,我这个人好办。你青年社通报这个情况,离开了团‘十大’筹备会。你们直接写信给中央,并没有通过筹备会转给我。不是和筹委会打官司,而是涉及到中央。天安门事件,华主席已经讲了。”
这时,他念了华国锋在1977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中关于天安门事件的“两个凡是”的段落。
他接着说:“刚才第一个是讲的组织观念。第二个讲文章内容符不符合华主席对天安门事件的估价。华主席在天安门问题上早就讲过,为什么有人还在上面纠缠?”
他说:“你叫我提意见我就提,第一期应该有毛主席的东西,应该考虑。华主席不在,叶副主席、聂帅题了字,我再给华主席讲讲,题个字嘛!毛主席逝世两周年,有总理的照片,主席的一个都没有,不考虑考虑?我说可以考虑一下。再有,我说里边有两篇文章内容与华主席讲话符合不符合,考虑考虑。再有,英雄人物不是不可以写,但是,天安门事件的性质已经定了。是你们记者写的文章,与转载不一样。”
他说:“为什么不发华主席的题词?华是毛主席的接班人,为什么不能等两天?”
他说:“一是不动了,就照你们的意见办,华主席题词也不登了。这是你们的意见。怕什么?最多只能说汪东兴讲的、韩英讲的、筹备会讲的都不灵嘛!最多说你们打了个胜仗。题词可以不登,主席诗词也不登。这一期,中央没有审查,就是中国青年社发出的,我声明,我没审查。第二条意见,把华主席题词、毛主席诗词三首和照片放进去,其他不动,因为动了也不行。我看这两个意见,不可能有第三个意见。”
他说:“历史上有教训,凡是离开党的领导,一事无成,会碰得头破血流。”
他说,“今天批评一下,说得不恰当,请你们原谅。我的心还是好的,不能说你对我错了,都对。”
总编辑火速派人赴印刷厂,为每册尚未发表的《中国青年》夹进华国锋题词、毛泽东诗词重印,又收回已发出的4万多份。
第二节 三中全会改变中国邓小平成领导核心(2)
各路“诸侯”陆续表态
真理标准的讨论,很快就从北京向四面八方辐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负责人都在严肃地思考这个问题,有的爽快了当,有的颇费踌躇;这倒并不因为这个问题在理论上有什么深奥难懂之处,关键在于“妾身未分明”――拿不准在政治上究竟采取何种态度为宜。当然,问题本身所牵连底蕴之深,所包容方面之广,也给这些在各色各样的战场上出生入死,翻上滚下的豪杰们一些为难。
在这个问题上,最先明确亮出自己的观点的是,当时的辽宁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和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杨易辰。
任仲夷在辽宁省委主办的理论月刊《理论与实践》第八、九期合刊上发表文章,题目是:
《理论上根本的拨乱反正》。
以后其他省、市、自治区的第一书记和各大军区的主要负责人,纷纷在各种会议上发表讲话,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新华社一一播发消息,首都报纸则作为要闻争相刊登。
按照新华社报道的时间,依次是:
8月27日汪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
9月10日廖志高福建省委第一书记
9月19日习仲勋广东省委第二书记
9月24日铁瑛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李本平浙江省委书记
9月27日江渭清江西省委第一书记
10月3日刘子厚河北省委第一书记
10月5日谭启龙青海省委第一书记
10月8日王铎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