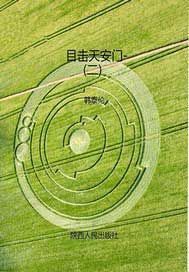第64章 三进三出中南海!小平光辉烛千秋(7)
“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
中国知识分子胆子最小,不是吗?
当前,我们的科技成果,除那些攀高峰的项目外,再不能只写文章、专著或搞评奖。否则,科技人员的辛勤劳动就会功亏一篑。
多么希望一部分科技人员成为科技企业家、实业家、科技经纪人,使我国科技成果尽快实现商品化、产业化、国际化。
“中国科技人员在攻关上势在必得,但在开发市场上却是书生气十足。”
著名学者杨振宁说得有道理吗?
发展经济,靠人力、物力、财力的增加,投入多、产出少。
这条粗放式道路看来是走不下去了。
因为这样,你会永远落后。穷的愈穷,富的愈富。
靠剥夺农民,靠侵略或压迫第三世界,行吗?
出售资源,只发展劳动密集型行业,靠“引进”来购买现代化,行吗?
看来,我们只能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来发展经济的道路。
我国资源相对缺乏,靠大量消耗资源来发展经济是没有出路的。
人口增加,耕地减少,离开科技,农业很难再上新台阶。
设备陈旧,工艺落后,离开科技,工业很难走出质量差、成本高、效益低的困境。
现代战争日益进入高科技较量,离开科技,国防实力很难有显著的增强。
向科技索取效益、向教育索要人才!
这是当今世界发展经济惟一现实而有效的途径。
不论是什么样的政治立场,不论是什么信仰,也不论是穷国和富国,它不分地区、民族,不受资源的限制,凡是经济增长快的国家都是走同一的道路。
谁先认识到,谁起步早,投入大,发展就快;否则,贫困、落后的局面难以摆脱。
今后十年我国粮食生产要爬两个台阶,这个目标能不能实现?江泽民在四川看了一圈。又同农业专家进行了座谈,他“越来越有信心”。
“只要努力是完全可以实现的”,“宝”就主要押在科学技术上。
1842年马克思、恩格斯敲响了资本主义的丧钟。
可资本主义至今还没死,还和平演变了社会主义。
他们靠的是什么?
1978年,邓小平访问日本,在高速列车上,他说:“这列车走得很快,我好像被人推了一下,我们需要这样。”
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中永远充满活力的源泉。资本主义在战后没有死,反而有较快的发展速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致力于发展科学技术,从而促进了经济的增长。
据统计,战后30多年来,促使经济增长的各因素中,科学技术的比重美国为71%,日本为65%,西德为68%。
早在60年代初,当时的美国总统肯尼迪就说,哪一个国家能控制宇宙就能控制地球。日本松下电器公司有一个自行车公司,只有20名雇员,1台计算机,却能生产18个型号、1000万种不同款式的自行车。从赛车、公路车到山地车,无所不包,而且有119种颜色和图案,尺寸规格几乎同顾客的需求一样多。你要买自行车,可先提出你个人的要求,工厂测量你的身材,3分钟后就画出了你所要的自行车样图,3小时内就提供给你自行车了。
我们可以想象,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生产方式和什么样的生产速度!
社会主义能不能代替资本主义,他们似乎早就懂得“最终可能是科学解决问题。”
科学技术是资本主义的对手,不是我们!
我们的对手是科学技术吗?还是资本主义制度?深圳潘强恩有一个颇为形象的譬喻,他说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好像一道堤分隔开的两股水,不管堤筑得多么高、多么厚实,都难免高水位向低水位渗透,而防止这种渗透的最佳办法,就是低的一方使自己的水位也提高,高到与对方持平,进而高过对方。
少谈些主义,多解决些问题。
再不要在“姓资”“姓社”上争论了。
资本主义最高兴我们干这个。
对第一号特区强有力的支持
在深圳特区孕育、诞生以及十多年来走过的蹒跚、坎坷而又坚定、奋进的道路上,烙刻着一位伟人深邃关切的目光、高瞻远瞩的睿智和稳实的脚印。
他,就是特区的缔造者、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
1978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拨正了中国前进的航向。“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已成为10亿人共同的行动。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人物邓小平提出,中国经济之大鹏要腾飞,必须借助改革、开放这两翼。
八亿农民掀起的改革大潮已开始涌动,“包产到户”不再是洪水猛兽。那么,中国对外开放的突破口在哪儿呢?
1979年4月,北京,中央工作会议。会议主要讨论调整国民经济等问题,提出了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
在会议上,当时担任广东省委主要领导工作的习仲勋、杨尚昆向中央汇报工作,提出一个建议:广东临近港澳,可以发挥这一优势,在对外开放上做点文章。
会议期间,邓小平同他们进行了谈话。
话题从延安谈起。谈到当年那么小小的一块边区,后来竟打出这么大一块江山;谈到解放几十年了,老边区人民还不富裕。谈话者不禁感慨万分。
邓小平陷入了沉思。然后,他说出了一句应当为后人载入史册的话:“你们上午的那个汇报不错嘛,在你们广东划出一块地方来,也搞一个特区,怎么样?”
他说:“办一个特区。过去陕甘宁就是特区嘛。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中央工作会议后不久,广东、福建两省委分别于1979年6月6日、6月9日写出了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报告,呈送中央。
7月15日,中央、国务院批转了两省委报告,确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试办特区。
1980年3月,中央在广州召开广东、福建两省参加的会议。正式将“出口特区”定名为“经济特区”。
8月,全国人大召开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并颁布《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公开宣布:“在深圳、珠海、汕头三市,分别划出一定区域,设置经济特区。”
1979年,一批勇于“吃蟹”的创业者,进驻那条不宽的深圳河的北面,开始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尝试――筹建特区。
1980年8月26日,那个如今被全世界当作热门话题谈论的南中国海边的小城,响起一片噼噼叭叭的爆炸声。在这片热闹的爆竹声中,中国第一批经济特区中的第一号特区――深圳经济特区诞生了!
1984年1月24日,距农历春节还有七天。紫荆花在特区的路旁已绽开紫红色的花朵,象征吉祥喜庆的盆盆金桔摆上了特区人居室的阳台。在深圳特区诞生后的第五个春天的这个中午,邓小平迈着轻快稳健的步伐,踏上了中国改革开放前沿地带的这片热土。
汽车驶向深圳迎宾馆桂园别墅。路上,邓小平按捺不住急切的心情,几次轻轻地拨开车窗的纱帘,注视着一掠而过的楼群、工地、人流……
他说:“经济特区是我的提议,中央的决定。5年了,到底怎么样,我要来看看。”
下午,在迎宾馆6号楼会议室,邓小平听取深圳市委的工作汇报。
当时的市委书记、市长梁湘站在特区规划示意图前,介绍着深圳特区自然状况、5年来引进外资、基建工程进展的情况。梁湘说,几年来特区工农业产值、财政收入增长很快,1982年工业产值为36000万元,1983年达到72000千万元。
“那就是一年翻了一番喽?”邓小平问。
梁湘答:“是翻了一番,比办特区前的1978年增长了10倍多。财政收入也比4年前增长了10倍,去年达到3亿多。”
邓小平满意地点点头。
听完市委的汇报,邓小平乘车来到刚刚竣工开业的国际商业大厦。在商场忙于采购年货的特区人发现了身穿深灰色便服的邓小平,喜出望外,热烈鼓掌欢迎。
邓小平登上20层高的国商大厦楼顶,俯瞰正在建设中的罗湖新城区。他的面前,矗立着已经建成和正在施工的60多幢18层以上的高楼群。在特区的规划图上,罗湖区将成为特区的商业金融中心。
邓小平的目光落在马路对面正在施工的国贸大厦。这座后来被誉为“神州第一楼”、高53层的现代化建筑,此时正以“三天一层楼”的速度升腾。特区的建设者在国内率先采用大面积滑模的先进施工工艺,在这儿创立了蜚声中外的“深圳速度”。
天色已近黄昏,一抹晚霞映照着生机勃勃的特区。邓小平推开陪同人员送上的大衣,迎着阵阵北风,目光由近及远,久久注视着整个特区。
他说:“看见了,我都看清楚了。”他对特区的建设发展速度表示满意。
25日上午,邓小平来到深圳河畔的渔民村访问。身穿崭新呢大衣的村党支部书记吴伯森激动地把客人引进自己别墅式的楼房里。这幢楼房上下两层,180平方米,有两个客厅、6间卧室,还有饭厅、厨房、卫生间,楼上楼下的客厅里各摆一台彩电和收录机。
邓小平问吴伯森:“你现在什么都有了吧?”吴伯森说:“都有了。做梦也没想到能有今天这样的好日子。”他再三感谢党的富民政策。
吴伯森将客人引到一口池塘边,指着一排养鸭的水上茅棚说:“这是60年代以前群众住过的房子,现在都给鸭子住了。”他介绍道:去年全村年收入达47万元,人均年收入2800元,每个劳动力年收入5970元,劳动力月均收入439元。
这时,陪同人员对邓小平说:“比您的工资还高呢。”邓小平略一沉吟,说:“全国农村要过上这样的生活,恐怕还要100年。”他又说,像深圳发展得这样快,也得要50年。
25日下午,邓小平参观了上步工业区深圳中航技术进出口公司。当邓小平走进这家电子厂的防尘、恒温车间时,车间工人和技术人员在计算机屏幕上打出“振兴中华,勤奋工作,向四化进军”的字幕,表达他们对这位中国改革开放总决策者的衷心感激。
邓小平兴致勃勃地观看了人和计算机下象棋的表演。在听取该厂关于搞电脑软件开发、发展智力密集型产品的企业发展情况汇报后,邓小平高兴地说:有一位美籍华裔学者告诉我,美国搞电脑软件编制的都是一批娃娃、学生;他还建议我们要重视培训青少年。全中国有那么多娃娃、学生,搞软件是完全有这个条件的。
26日上午,邓小平来到濒临深圳湾的蛇口工业区办公大楼。他看了工业区全景的模型后,指着窗外蛇口港码头问工业区领导袁庚:码头是什么时候建成的?能停多少吨位的船?袁庚一一作了回答。
袁庚特别提到,办特区以前,蛇口是人口外流外逃的口子。办了特区以后,不但人员不外流了,相反,现在是人才回流、资金回流。几年来由客商独资或合资兴办了47家企业,其中30家已投产,10家开始盈利。企业职工工资水平已超过澳门。袁庚说,蛇口改革了劳动人事制度,实行招聘和合同制,实行职务工资和浮动工资。几年来的实践,我们体会最深的是:劳动人事制度的改革要同工资制度的改革同步进行,精神文明建设和物质文明建设要同步进行。听罢,邓小平微笑颔首。
在蛇口工业区,邓小平首先视察了微波通讯站,而后到合资经营的华益铝格厂和海上旅游中心参观。邓小平为我国首座海上旅游中心挥毫写下了“海上世界”四个字。
几天的实地考察,邓小平对特区这一新生事物的旺盛生命力有了更直接的感触。离开深圳到达广州,他欣然提笔,为深圳特区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
1984年2月中旬,邓小平结束对深圳、珠海、厦门三特区的视察,返回北京。
2月25日,经过深思熟虑,邓小平与几位中央领导进行了谈话。
邓小平说:“这次我到深圳一看,给我的印象是一片兴旺发达景象。深圳的建设速度相当快。其中蛇口更快,原因是给了他们一点权力,500万美元以下的开支可以自己做主。他们的口号是‘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深圳盖房子,几天就是一层,一幢大楼没有多少天就盖起来了。那里的施工队伍还是内地去的,效率高的原因是搞了承包制,赏罚分明。”
他还说:“听说深圳治安比过去好了,跑到香港的人开始回来,原因之一是就业多,收入增加了,物质条件也好多了,说明精神文明是从物质文明来的嘛!”
说着,邓小平的神色严肃起来,“我们建立特区,实行开放政策,有个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特区是个窗口,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从特区可以引进技术,获得知识,学到管理,管理也是知识。”“特区将成为开放的基地,不仅在经济方面、培养人才方面得到好处,而且会扩大我们的对外影响。”
他缓了口气,话题又落到深圳特区上来,“在深圳那里现在至少有两件事情可以搞,一个是建核电站,一个是吸引华侨投资办所大学。华侨在那里办大学,由他们聘请国外水平高的教授,从国外购买教学设备,这样可以给我们培养一批人才。”
1984年,深圳尚处于初创、起步阶段。一些人对它怀疑,有人非议。各种困难和阻力,挡在深圳刚刚抬起的脚步前。
但深圳和深圳人是幸运的。邓小平在最关键的时刻对深圳予以最强有力的支持。深圳不再为各种议论的纷扰而忐忑不安。
1985年7月15日,人民大会堂。隔着摆放茶杯的茶几,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总理钱伯斯与邓小平分坐在宾、主席上。作为老朋友,会谈的气氛是亲切融洽的。
十年前,钱伯斯访问中国时,曾见过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邓小平。十年后再次来访,钱伯斯感触最深的有两点:一是中国几年来的改革开放,产生了令人振奋的大变化;二是81岁高龄的邓小平,竟如此身体硬朗、精神饱满。他对这两点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钱伯斯毫不掩饰对邓小平的身体健康的羡慕,问邓小平:“我想请教一下,您保持身体健康的秘诀是什么?”
邓小平笑了,说:“许多客人问过我,我的回答是四个字:‘乐观主义’。天塌下来不要紧,有人顶着。”他说:“我是三上三下的人,对什么问题都持乐观的态度,相信自己的信念总会实现。如果没有这样的信念,我是活不到今天的。”
钱伯斯说:“十年前我曾访问过中国,这次我们看到中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邓小平说:“变化是有的,但还是小变化。10年或15年以后,我们的变化可能会更显著一些。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走的是一条新路。我们的开放政策、其他一系列经济政策以及全面的体制改革都是一种试验”。邓小平强调:开放政策和经济体制改革一定要坚持下去,不能变化。变就意味着没有出路。我相信我们的政策是会成功的。
钱伯斯认真地听着。他对邓小平说:“你对自己的政策保持如此的信念,使我十分钦佩。”他告诉邓小平,他将前往深圳特区参观。
邓小平说,深圳经济特区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试验。现在看来,我们原来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
第一节 改革开放后人忆鞠躬尽瘁耀中华(3)
他又说,你们可以看到深圳的发展是很快的,但这毕竟是一个试验。现在还有一些问题没有解决。不过,特区开始才三年多一些时间,再过三年总会找出办法来解决这些问题。
邓小平对深圳特区的情况了如指掌。就如他当年运筹帷幄、指挥声势浩大的淮海战役,熟悉战区内的每一条河流、每一个村庄,熟悉敌我双方的兵力部署、攻守态势。在肯定深圳特区建设成就的同时,他以极其敏锐的洞察力透析着深圳异乎寻常的发展速度背后隐藏着的问题。他在提醒深圳,在鼓励深圳开拓新路子。
正如邓小平所预料的,1985年的深圳,在几年的高速发展之后,经济过热、效益偏低等问题似退潮后的礁石,显露出来。
适逢全国进行信贷、基建压缩,深圳的一些建设项目因资金拮据不得不中途杀车。一些外商以为中国特区政策要变,相继抽走投资……深圳的双肩感到了沉重的压力。深圳走到了历史发展的一个十字路口,面临着严峻的抉择。
作为承担四个“窗口”责任、探索中国开放之路的排头兵,深圳没有退路。深圳开始了痛苦的反思,新的艰辛尝试。深圳的眼睛开始越过南中国海,越过太平洋,投向国际市场。深圳决定:发展以工业为主的外向型经济!
1985年8月1日,人民解放军的建军节。避暑胜地北戴河,清凉的海风驱走了酷暑炎热。
在一幢外表朴素、绿阴掩映的建筑里,邓小平会见了竹入义胜及其率领的日本公明党第13次访华代表团。会谈长达70分钟,讨论的一个重要议题是经济特区问题。
邓小平说:“前不久我对一位外国客人说,深圳是个试验,外面就有人怀疑,说什么中国的政策是不是又要改变,是不是我否定了原来的判断,建立经济特区的话是不是改变了。所以,现在我要肯定两句话:第一句话是,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第二句话是,深圳经济特区还是一个试验。这两句话并不矛盾。我们的整个开放政策也是一个试验,从世界的角度上来讲,也是一个大试验。”
邓小平充满信心地说:“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是坚定不移的,但我们在开放过程中要小心谨慎。我们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一定要保持谦逊的态度。”
竹入义胜说:“你的话非常明确,全世界的人听了以后都会放心的。”
更放心的是深圳。它的外向型经济的发展方向得到了邓小平的首肯。深圳人振奋了,他们有了向新的目标奋进的信心和力量。
时间进入1987年6月12日,在庄严肃穆的人民大会堂内,典雅的吊灯泻下的柔和的光,摄影灯频频闪烁的光,充盈着会见厅。南斯拉夫贵宾科罗舍茨紧紧地握着邓小平的手。双方都为能有这样一个机会交流两国的建设经验感到高兴。
邓小平向客人详细地描述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
谈到开放政策时,他说:“我们首先搞了深圳经济特区。开始的时候广东提出搞特区,我同意了他们的意见,我说名字叫经济特区,搞政治特区就不好了。”
邓小平再次提到1984年的深圳之行,并为他在深圳的题词的深刻内涵作了最准确的注解:“我去过一次深圳,那里确实是一派兴旺气象。当时他们让我题词,我写道:‘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当时我们党内还有人采取怀疑的态度,香港舆论界不管是反对我们的还是赞成我们的,也都有人持怀疑态度,不相信我们是正确的。深圳搞了七八年了,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他接着说:“当然一个完全新的事物不允许犯错误是不行的,有一点错误也是很小的。他们自己总结经验,由内向型转为外向型,这样就能够变成工业基地,并能够打进国际市场。这一点明确以后,也不过两三年的时间,就改变了面貌。深圳的同志告诉我,那里的工业产品50%以上出口,外汇收支可以平衡。”
邓小平打了个手势,提高了声音:“现在我可以放胆地说,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决定不仅是正确的,而且是成功的。所有的怀疑都可以消除了。”
这铿锵有力的声音,如隆隆的雷声滚过神州大地。
自由港:小平送给厦门的一个大政策
1993年6月1日,祖国的花朵,沉浸在欢乐的节日中。
同一天,北京饭店会议厅,加快厦门改革开放研讨会气氛热烈。在中国世界观察研究所和经济日报联合主办的这个会上,群贤毕至,少长咸集,大家共同发出了一个声音,在当前抓住机遇、深化改革、加快发展的新形势下,应该进一步贯彻落实邓小平同志关于再造几个香港的战略构想和十年前提出建设厦门自由港的精神,加快厦门建成自由港的探索和实践的步伐。专家们说,厦门打出“自由港”的旗号,此其时矣!千万不能再等了!
“厦庇五洲客,门收万顷涛”。厦门建造自由港,可以追溯到十年前。
1984年2月初,北国还是冰封雪飘,厦门则是一片翠绿。木棉花吐出点点猩红,玫瑰、茶花、蔷薇,争芳斗艳。
2月7日上午,一列火车驶进鹭岛,邓小平来到了厦门。项南等省市领导人迎上前去:
“欢迎您,小平同志!”
在从火车站到宾馆的路上,邓小平边看边听项南等同志的介绍,心情兴奋。在此之前,一月下旬,邓小平视察了深圳、珠海,看到一片兴旺发达景象。明确了一个指导思想,建立经济特区,实行开放政策,不是收,而是放。他欣然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珠海经济特区好。”
2月8日,邓小平视察了东渡港码头。那高大的橘黄色龙门吊车,那一排排色彩鲜明的集装箱,那一艘艘装卸货物的远洋货轮,都使他强烈感到厦门经济特区的繁忙景象。
离开东渡港,邓小平登上“鹭江”号游艇,项南坐在小平同志身边。
项南对邓小平说:“小平同志,厦门特区现在实际只有2.5平方公里,实在太小了,太束缚手脚了,即使很快全部建成,也没有多大的实际意义。”
邓小平注视着他和省市的负责同志,“你们的意思是……”
“把特区扩大到全岛!”项南明确坚定地回答,“使整个厦门岛都开放,这对引进外资和技术,对改造全岛的老企业,对加强海峡两岸的交往,都可以起到更大的作用。”
邓小平一边听,一边察看地图,肯定地说:“我看可以,这没得啥子问题嘛!”
当看到厦门离金门这样近时,邓小平问:怎样才能使两地直来直往?
项南回答:搞自由港。
项南说:“现在台湾人到大陆,都不是直来直去,要从香港或日本绕道来,这太麻烦了。如果把离台湾、金门最近的厦门变成自由港,实行进出自由,这对海峡两岸中国人的交往,会起很大的促进作用。”
王震在一旁说:“应该考虑这个问题。”
邓小平很快说:“可以考虑。”邓小平接着问:“自由港,实行哪些政策呢?”
中国知识分子胆子最小,不是吗?
当前,我们的科技成果,除那些攀高峰的项目外,再不能只写文章、专著或搞评奖。否则,科技人员的辛勤劳动就会功亏一篑。
多么希望一部分科技人员成为科技企业家、实业家、科技经纪人,使我国科技成果尽快实现商品化、产业化、国际化。
“中国科技人员在攻关上势在必得,但在开发市场上却是书生气十足。”
著名学者杨振宁说得有道理吗?
发展经济,靠人力、物力、财力的增加,投入多、产出少。
这条粗放式道路看来是走不下去了。
因为这样,你会永远落后。穷的愈穷,富的愈富。
靠剥夺农民,靠侵略或压迫第三世界,行吗?
出售资源,只发展劳动密集型行业,靠“引进”来购买现代化,行吗?
看来,我们只能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来发展经济的道路。
我国资源相对缺乏,靠大量消耗资源来发展经济是没有出路的。
人口增加,耕地减少,离开科技,农业很难再上新台阶。
设备陈旧,工艺落后,离开科技,工业很难走出质量差、成本高、效益低的困境。
现代战争日益进入高科技较量,离开科技,国防实力很难有显著的增强。
向科技索取效益、向教育索要人才!
这是当今世界发展经济惟一现实而有效的途径。
不论是什么样的政治立场,不论是什么信仰,也不论是穷国和富国,它不分地区、民族,不受资源的限制,凡是经济增长快的国家都是走同一的道路。
谁先认识到,谁起步早,投入大,发展就快;否则,贫困、落后的局面难以摆脱。
今后十年我国粮食生产要爬两个台阶,这个目标能不能实现?江泽民在四川看了一圈。又同农业专家进行了座谈,他“越来越有信心”。
“只要努力是完全可以实现的”,“宝”就主要押在科学技术上。
1842年马克思、恩格斯敲响了资本主义的丧钟。
可资本主义至今还没死,还和平演变了社会主义。
他们靠的是什么?
1978年,邓小平访问日本,在高速列车上,他说:“这列车走得很快,我好像被人推了一下,我们需要这样。”
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中永远充满活力的源泉。资本主义在战后没有死,反而有较快的发展速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致力于发展科学技术,从而促进了经济的增长。
据统计,战后30多年来,促使经济增长的各因素中,科学技术的比重美国为71%,日本为65%,西德为68%。
早在60年代初,当时的美国总统肯尼迪就说,哪一个国家能控制宇宙就能控制地球。日本松下电器公司有一个自行车公司,只有20名雇员,1台计算机,却能生产18个型号、1000万种不同款式的自行车。从赛车、公路车到山地车,无所不包,而且有119种颜色和图案,尺寸规格几乎同顾客的需求一样多。你要买自行车,可先提出你个人的要求,工厂测量你的身材,3分钟后就画出了你所要的自行车样图,3小时内就提供给你自行车了。
我们可以想象,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生产方式和什么样的生产速度!
社会主义能不能代替资本主义,他们似乎早就懂得“最终可能是科学解决问题。”
科学技术是资本主义的对手,不是我们!
我们的对手是科学技术吗?还是资本主义制度?深圳潘强恩有一个颇为形象的譬喻,他说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好像一道堤分隔开的两股水,不管堤筑得多么高、多么厚实,都难免高水位向低水位渗透,而防止这种渗透的最佳办法,就是低的一方使自己的水位也提高,高到与对方持平,进而高过对方。
少谈些主义,多解决些问题。
再不要在“姓资”“姓社”上争论了。
资本主义最高兴我们干这个。
对第一号特区强有力的支持
在深圳特区孕育、诞生以及十多年来走过的蹒跚、坎坷而又坚定、奋进的道路上,烙刻着一位伟人深邃关切的目光、高瞻远瞩的睿智和稳实的脚印。
他,就是特区的缔造者、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
1978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拨正了中国前进的航向。“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已成为10亿人共同的行动。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人物邓小平提出,中国经济之大鹏要腾飞,必须借助改革、开放这两翼。
八亿农民掀起的改革大潮已开始涌动,“包产到户”不再是洪水猛兽。那么,中国对外开放的突破口在哪儿呢?
1979年4月,北京,中央工作会议。会议主要讨论调整国民经济等问题,提出了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
在会议上,当时担任广东省委主要领导工作的习仲勋、杨尚昆向中央汇报工作,提出一个建议:广东临近港澳,可以发挥这一优势,在对外开放上做点文章。
会议期间,邓小平同他们进行了谈话。
话题从延安谈起。谈到当年那么小小的一块边区,后来竟打出这么大一块江山;谈到解放几十年了,老边区人民还不富裕。谈话者不禁感慨万分。
邓小平陷入了沉思。然后,他说出了一句应当为后人载入史册的话:“你们上午的那个汇报不错嘛,在你们广东划出一块地方来,也搞一个特区,怎么样?”
他说:“办一个特区。过去陕甘宁就是特区嘛。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中央工作会议后不久,广东、福建两省委分别于1979年6月6日、6月9日写出了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报告,呈送中央。
7月15日,中央、国务院批转了两省委报告,确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试办特区。
1980年3月,中央在广州召开广东、福建两省参加的会议。正式将“出口特区”定名为“经济特区”。
8月,全国人大召开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并颁布《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公开宣布:“在深圳、珠海、汕头三市,分别划出一定区域,设置经济特区。”
1979年,一批勇于“吃蟹”的创业者,进驻那条不宽的深圳河的北面,开始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尝试――筹建特区。
1980年8月26日,那个如今被全世界当作热门话题谈论的南中国海边的小城,响起一片噼噼叭叭的爆炸声。在这片热闹的爆竹声中,中国第一批经济特区中的第一号特区――深圳经济特区诞生了!
1984年1月24日,距农历春节还有七天。紫荆花在特区的路旁已绽开紫红色的花朵,象征吉祥喜庆的盆盆金桔摆上了特区人居室的阳台。在深圳特区诞生后的第五个春天的这个中午,邓小平迈着轻快稳健的步伐,踏上了中国改革开放前沿地带的这片热土。
汽车驶向深圳迎宾馆桂园别墅。路上,邓小平按捺不住急切的心情,几次轻轻地拨开车窗的纱帘,注视着一掠而过的楼群、工地、人流……
他说:“经济特区是我的提议,中央的决定。5年了,到底怎么样,我要来看看。”
下午,在迎宾馆6号楼会议室,邓小平听取深圳市委的工作汇报。
当时的市委书记、市长梁湘站在特区规划示意图前,介绍着深圳特区自然状况、5年来引进外资、基建工程进展的情况。梁湘说,几年来特区工农业产值、财政收入增长很快,1982年工业产值为36000万元,1983年达到72000千万元。
“那就是一年翻了一番喽?”邓小平问。
梁湘答:“是翻了一番,比办特区前的1978年增长了10倍多。财政收入也比4年前增长了10倍,去年达到3亿多。”
邓小平满意地点点头。
听完市委的汇报,邓小平乘车来到刚刚竣工开业的国际商业大厦。在商场忙于采购年货的特区人发现了身穿深灰色便服的邓小平,喜出望外,热烈鼓掌欢迎。
邓小平登上20层高的国商大厦楼顶,俯瞰正在建设中的罗湖新城区。他的面前,矗立着已经建成和正在施工的60多幢18层以上的高楼群。在特区的规划图上,罗湖区将成为特区的商业金融中心。
邓小平的目光落在马路对面正在施工的国贸大厦。这座后来被誉为“神州第一楼”、高53层的现代化建筑,此时正以“三天一层楼”的速度升腾。特区的建设者在国内率先采用大面积滑模的先进施工工艺,在这儿创立了蜚声中外的“深圳速度”。
天色已近黄昏,一抹晚霞映照着生机勃勃的特区。邓小平推开陪同人员送上的大衣,迎着阵阵北风,目光由近及远,久久注视着整个特区。
他说:“看见了,我都看清楚了。”他对特区的建设发展速度表示满意。
25日上午,邓小平来到深圳河畔的渔民村访问。身穿崭新呢大衣的村党支部书记吴伯森激动地把客人引进自己别墅式的楼房里。这幢楼房上下两层,180平方米,有两个客厅、6间卧室,还有饭厅、厨房、卫生间,楼上楼下的客厅里各摆一台彩电和收录机。
邓小平问吴伯森:“你现在什么都有了吧?”吴伯森说:“都有了。做梦也没想到能有今天这样的好日子。”他再三感谢党的富民政策。
吴伯森将客人引到一口池塘边,指着一排养鸭的水上茅棚说:“这是60年代以前群众住过的房子,现在都给鸭子住了。”他介绍道:去年全村年收入达47万元,人均年收入2800元,每个劳动力年收入5970元,劳动力月均收入439元。
这时,陪同人员对邓小平说:“比您的工资还高呢。”邓小平略一沉吟,说:“全国农村要过上这样的生活,恐怕还要100年。”他又说,像深圳发展得这样快,也得要50年。
25日下午,邓小平参观了上步工业区深圳中航技术进出口公司。当邓小平走进这家电子厂的防尘、恒温车间时,车间工人和技术人员在计算机屏幕上打出“振兴中华,勤奋工作,向四化进军”的字幕,表达他们对这位中国改革开放总决策者的衷心感激。
邓小平兴致勃勃地观看了人和计算机下象棋的表演。在听取该厂关于搞电脑软件开发、发展智力密集型产品的企业发展情况汇报后,邓小平高兴地说:有一位美籍华裔学者告诉我,美国搞电脑软件编制的都是一批娃娃、学生;他还建议我们要重视培训青少年。全中国有那么多娃娃、学生,搞软件是完全有这个条件的。
26日上午,邓小平来到濒临深圳湾的蛇口工业区办公大楼。他看了工业区全景的模型后,指着窗外蛇口港码头问工业区领导袁庚:码头是什么时候建成的?能停多少吨位的船?袁庚一一作了回答。
袁庚特别提到,办特区以前,蛇口是人口外流外逃的口子。办了特区以后,不但人员不外流了,相反,现在是人才回流、资金回流。几年来由客商独资或合资兴办了47家企业,其中30家已投产,10家开始盈利。企业职工工资水平已超过澳门。袁庚说,蛇口改革了劳动人事制度,实行招聘和合同制,实行职务工资和浮动工资。几年来的实践,我们体会最深的是:劳动人事制度的改革要同工资制度的改革同步进行,精神文明建设和物质文明建设要同步进行。听罢,邓小平微笑颔首。
在蛇口工业区,邓小平首先视察了微波通讯站,而后到合资经营的华益铝格厂和海上旅游中心参观。邓小平为我国首座海上旅游中心挥毫写下了“海上世界”四个字。
几天的实地考察,邓小平对特区这一新生事物的旺盛生命力有了更直接的感触。离开深圳到达广州,他欣然提笔,为深圳特区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
1984年2月中旬,邓小平结束对深圳、珠海、厦门三特区的视察,返回北京。
2月25日,经过深思熟虑,邓小平与几位中央领导进行了谈话。
邓小平说:“这次我到深圳一看,给我的印象是一片兴旺发达景象。深圳的建设速度相当快。其中蛇口更快,原因是给了他们一点权力,500万美元以下的开支可以自己做主。他们的口号是‘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深圳盖房子,几天就是一层,一幢大楼没有多少天就盖起来了。那里的施工队伍还是内地去的,效率高的原因是搞了承包制,赏罚分明。”
他还说:“听说深圳治安比过去好了,跑到香港的人开始回来,原因之一是就业多,收入增加了,物质条件也好多了,说明精神文明是从物质文明来的嘛!”
说着,邓小平的神色严肃起来,“我们建立特区,实行开放政策,有个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特区是个窗口,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从特区可以引进技术,获得知识,学到管理,管理也是知识。”“特区将成为开放的基地,不仅在经济方面、培养人才方面得到好处,而且会扩大我们的对外影响。”
他缓了口气,话题又落到深圳特区上来,“在深圳那里现在至少有两件事情可以搞,一个是建核电站,一个是吸引华侨投资办所大学。华侨在那里办大学,由他们聘请国外水平高的教授,从国外购买教学设备,这样可以给我们培养一批人才。”
1984年,深圳尚处于初创、起步阶段。一些人对它怀疑,有人非议。各种困难和阻力,挡在深圳刚刚抬起的脚步前。
但深圳和深圳人是幸运的。邓小平在最关键的时刻对深圳予以最强有力的支持。深圳不再为各种议论的纷扰而忐忑不安。
1985年7月15日,人民大会堂。隔着摆放茶杯的茶几,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总理钱伯斯与邓小平分坐在宾、主席上。作为老朋友,会谈的气氛是亲切融洽的。
十年前,钱伯斯访问中国时,曾见过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邓小平。十年后再次来访,钱伯斯感触最深的有两点:一是中国几年来的改革开放,产生了令人振奋的大变化;二是81岁高龄的邓小平,竟如此身体硬朗、精神饱满。他对这两点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钱伯斯毫不掩饰对邓小平的身体健康的羡慕,问邓小平:“我想请教一下,您保持身体健康的秘诀是什么?”
邓小平笑了,说:“许多客人问过我,我的回答是四个字:‘乐观主义’。天塌下来不要紧,有人顶着。”他说:“我是三上三下的人,对什么问题都持乐观的态度,相信自己的信念总会实现。如果没有这样的信念,我是活不到今天的。”
钱伯斯说:“十年前我曾访问过中国,这次我们看到中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邓小平说:“变化是有的,但还是小变化。10年或15年以后,我们的变化可能会更显著一些。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走的是一条新路。我们的开放政策、其他一系列经济政策以及全面的体制改革都是一种试验”。邓小平强调:开放政策和经济体制改革一定要坚持下去,不能变化。变就意味着没有出路。我相信我们的政策是会成功的。
钱伯斯认真地听着。他对邓小平说:“你对自己的政策保持如此的信念,使我十分钦佩。”他告诉邓小平,他将前往深圳特区参观。
邓小平说,深圳经济特区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试验。现在看来,我们原来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
第一节 改革开放后人忆鞠躬尽瘁耀中华(3)
他又说,你们可以看到深圳的发展是很快的,但这毕竟是一个试验。现在还有一些问题没有解决。不过,特区开始才三年多一些时间,再过三年总会找出办法来解决这些问题。
邓小平对深圳特区的情况了如指掌。就如他当年运筹帷幄、指挥声势浩大的淮海战役,熟悉战区内的每一条河流、每一个村庄,熟悉敌我双方的兵力部署、攻守态势。在肯定深圳特区建设成就的同时,他以极其敏锐的洞察力透析着深圳异乎寻常的发展速度背后隐藏着的问题。他在提醒深圳,在鼓励深圳开拓新路子。
正如邓小平所预料的,1985年的深圳,在几年的高速发展之后,经济过热、效益偏低等问题似退潮后的礁石,显露出来。
适逢全国进行信贷、基建压缩,深圳的一些建设项目因资金拮据不得不中途杀车。一些外商以为中国特区政策要变,相继抽走投资……深圳的双肩感到了沉重的压力。深圳走到了历史发展的一个十字路口,面临着严峻的抉择。
作为承担四个“窗口”责任、探索中国开放之路的排头兵,深圳没有退路。深圳开始了痛苦的反思,新的艰辛尝试。深圳的眼睛开始越过南中国海,越过太平洋,投向国际市场。深圳决定:发展以工业为主的外向型经济!
1985年8月1日,人民解放军的建军节。避暑胜地北戴河,清凉的海风驱走了酷暑炎热。
在一幢外表朴素、绿阴掩映的建筑里,邓小平会见了竹入义胜及其率领的日本公明党第13次访华代表团。会谈长达70分钟,讨论的一个重要议题是经济特区问题。
邓小平说:“前不久我对一位外国客人说,深圳是个试验,外面就有人怀疑,说什么中国的政策是不是又要改变,是不是我否定了原来的判断,建立经济特区的话是不是改变了。所以,现在我要肯定两句话:第一句话是,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第二句话是,深圳经济特区还是一个试验。这两句话并不矛盾。我们的整个开放政策也是一个试验,从世界的角度上来讲,也是一个大试验。”
邓小平充满信心地说:“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是坚定不移的,但我们在开放过程中要小心谨慎。我们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一定要保持谦逊的态度。”
竹入义胜说:“你的话非常明确,全世界的人听了以后都会放心的。”
更放心的是深圳。它的外向型经济的发展方向得到了邓小平的首肯。深圳人振奋了,他们有了向新的目标奋进的信心和力量。
时间进入1987年6月12日,在庄严肃穆的人民大会堂内,典雅的吊灯泻下的柔和的光,摄影灯频频闪烁的光,充盈着会见厅。南斯拉夫贵宾科罗舍茨紧紧地握着邓小平的手。双方都为能有这样一个机会交流两国的建设经验感到高兴。
邓小平向客人详细地描述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
谈到开放政策时,他说:“我们首先搞了深圳经济特区。开始的时候广东提出搞特区,我同意了他们的意见,我说名字叫经济特区,搞政治特区就不好了。”
邓小平再次提到1984年的深圳之行,并为他在深圳的题词的深刻内涵作了最准确的注解:“我去过一次深圳,那里确实是一派兴旺气象。当时他们让我题词,我写道:‘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当时我们党内还有人采取怀疑的态度,香港舆论界不管是反对我们的还是赞成我们的,也都有人持怀疑态度,不相信我们是正确的。深圳搞了七八年了,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他接着说:“当然一个完全新的事物不允许犯错误是不行的,有一点错误也是很小的。他们自己总结经验,由内向型转为外向型,这样就能够变成工业基地,并能够打进国际市场。这一点明确以后,也不过两三年的时间,就改变了面貌。深圳的同志告诉我,那里的工业产品50%以上出口,外汇收支可以平衡。”
邓小平打了个手势,提高了声音:“现在我可以放胆地说,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决定不仅是正确的,而且是成功的。所有的怀疑都可以消除了。”
这铿锵有力的声音,如隆隆的雷声滚过神州大地。
自由港:小平送给厦门的一个大政策
1993年6月1日,祖国的花朵,沉浸在欢乐的节日中。
同一天,北京饭店会议厅,加快厦门改革开放研讨会气氛热烈。在中国世界观察研究所和经济日报联合主办的这个会上,群贤毕至,少长咸集,大家共同发出了一个声音,在当前抓住机遇、深化改革、加快发展的新形势下,应该进一步贯彻落实邓小平同志关于再造几个香港的战略构想和十年前提出建设厦门自由港的精神,加快厦门建成自由港的探索和实践的步伐。专家们说,厦门打出“自由港”的旗号,此其时矣!千万不能再等了!
“厦庇五洲客,门收万顷涛”。厦门建造自由港,可以追溯到十年前。
1984年2月初,北国还是冰封雪飘,厦门则是一片翠绿。木棉花吐出点点猩红,玫瑰、茶花、蔷薇,争芳斗艳。
2月7日上午,一列火车驶进鹭岛,邓小平来到了厦门。项南等省市领导人迎上前去:
“欢迎您,小平同志!”
在从火车站到宾馆的路上,邓小平边看边听项南等同志的介绍,心情兴奋。在此之前,一月下旬,邓小平视察了深圳、珠海,看到一片兴旺发达景象。明确了一个指导思想,建立经济特区,实行开放政策,不是收,而是放。他欣然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珠海经济特区好。”
2月8日,邓小平视察了东渡港码头。那高大的橘黄色龙门吊车,那一排排色彩鲜明的集装箱,那一艘艘装卸货物的远洋货轮,都使他强烈感到厦门经济特区的繁忙景象。
离开东渡港,邓小平登上“鹭江”号游艇,项南坐在小平同志身边。
项南对邓小平说:“小平同志,厦门特区现在实际只有2.5平方公里,实在太小了,太束缚手脚了,即使很快全部建成,也没有多大的实际意义。”
邓小平注视着他和省市的负责同志,“你们的意思是……”
“把特区扩大到全岛!”项南明确坚定地回答,“使整个厦门岛都开放,这对引进外资和技术,对改造全岛的老企业,对加强海峡两岸的交往,都可以起到更大的作用。”
邓小平一边听,一边察看地图,肯定地说:“我看可以,这没得啥子问题嘛!”
当看到厦门离金门这样近时,邓小平问:怎样才能使两地直来直往?
项南回答:搞自由港。
项南说:“现在台湾人到大陆,都不是直来直去,要从香港或日本绕道来,这太麻烦了。如果把离台湾、金门最近的厦门变成自由港,实行进出自由,这对海峡两岸中国人的交往,会起很大的促进作用。”
王震在一旁说:“应该考虑这个问题。”
邓小平很快说:“可以考虑。”邓小平接着问:“自由港,实行哪些政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