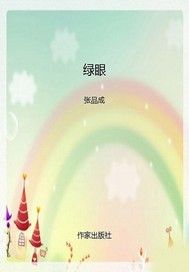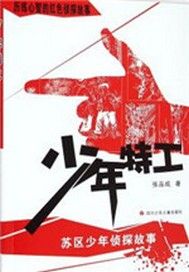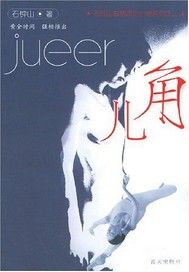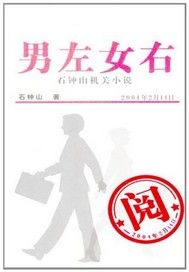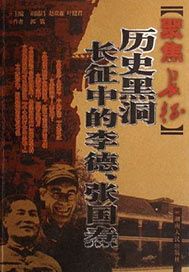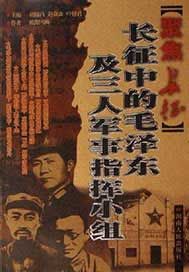第十二章 我所认识的权延赤
编辑部的同仁考虑到自本期刊物起将转载权延赤的一篇反映1959年“庐山事件”的重头文章,知我过去曾与其同在“一个战壕”,都是空军的专业作家,他在北京军区空军创作组,我在军委空军创作室,而且私交很好,过从甚密,故执意要我写篇对权延赤的印象。
我一听兀自犯难。因为越是朋友,越是交往频繁的朋友,越容易对彼此的言行举止“熟视无睹”,这就是往往出现的“墙内开花墙外香”的现象。还有,既然是老朋友,那么所披露的内容应该是鲜为人知的,对对方“质”的认识应该更冷僻,更独到,更深刻。不然,只择些许皮毛琐事,定会有辱“老友”称谓之崇高。
但是,为了刊物的“大局”需要,也就顾不得这许多了。于是,身为刊物主编的我便来个“恭敬不如从命”。
一
说权延赤是条硬汉子,倒不是指他身高一米八十开外的高大身躯和富有血性的殷红脸膛,也不是形容他那两道浓眉和声如狮吼的宏亮嗓音,而是说在长年的接触中,他首先给我“硬”的感觉,是他作为一名空军专业作家敢“硬”碰“硬”的创作。
“部队的作家写部队”,“空军的作家写空军”。这是部队主管文化艺术的部门几乎每年都要重申的口号。这个口号既是对部队专业作家的要求,又是检验作为一个部队专业作家的“硬性”尺度。虽然这个口号绝对没错,否则,“要是部队这么多作家都不写部队,那部队养这么多作家干什么”?谁又能说这句既是提问又是答案的话在逻辑上有什么谬误呢?既然作家是靠“养”,不报“养育”之恩岂不大逆不道?但是具体到创作上,几乎大多数作家都感到这个口号有点像孙猴子头上的“紧箍咒”,提起写部队题材就觉得头痛。因为对战争年代金戈铁马的生活该写的几乎都写过了,再写也难以写出新意,那么就只有在当代部队生活的田野里笔耕了。文艺的功能是“寓教于乐”。乐者,喜也,悦也,即兴致盎然之意。于文学作品,就是要设法让读者想看,爱看,以至达到“手不释卷”的程度,方为佳作。可是,和平建设期的部队生活,一没有刀光剑影,殊死搏杀,横扫千军;二没有运筹帷幄,指点江山,决胜千里;第三,反映部队生活题材的作品又要力避花前月下,缠缠绵绵,卿卿我我;特别是空军应该主要表现被誉为“天之骄子”的飞行员生活,可飞行员的真正舞台是驾驶歼击机在万米高空风驰电掣,作家本身一个个都是“旱鸭子”,怎么能对飞行员在空中的生活有切身的感受呢?没有感受到的东西却洋洋洒洒写成作品让读者去感受,不是地道的“挂羊头卖狗肉”么?还有一个极难言喻的原因,即部队是“柱石”,“柱石”是不能披露“斜度”和“阴影”的。所以,“要写又不好写”,“不写又不行”,因此大多数“聪明”的作家在两难之中有的搞“迂回战术”,有的巧用“嫁接技术”,有的索性来个“点缀法”,只要对付过去就行了。
然而,权延赤却不然。他从基层部队调到机关当专业作家,先是沉默了几年。据说是一连几个“猛子”扎到航空兵部队,待“厚积而薄发”。果然,权延赤不久便在部队“大哥大”刊物《解放军文艺》上发表出以“开天人”为系列的反映航空兵部队生活的中短篇小说,如春雷乍响,在沉寂的部队文坛激起巨大的波澜。接着,他又在河南人民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相继出版了反映空军生活的长篇小说《蔚蓝色的脚印》和《多欲之年》,可谓硕果累累。他那“硬”碰“硬”的“硬”劲儿,委实令“同好”还是原本就“不怎么好”的“笔杆子”们刮目相看了。当然,“同好”者多是钦佩与祝贺,“不怎么好”者则多是嫉妒与不屑了。
权延赤在创作生活中再一个敢于碰“硬”,则是有目共睹,抑或有口皆碑了。大凡诚实的人而不是文过饰非之辈都不会否认,权延赤在挥笔撰写《走下神坛的毛泽东》这部具有时代价值的纪实文学作品时,毛泽东的名字被当成咒骂和嘲弄的字眼儿为一些道貌岸然者和一些所谓屡经“浩劫”者所唾弃,那时的景况似乎谁诅咒毛泽东越耸人听闻越刻骨铭心谁就越伟大,越正确,越光彩。那时,我刚“解甲归田”转业到中国华侨出版公司不久,到权延赤家去约稿,得知他正奋笔疾书创作反映毛泽东生活的纪实性作品。当言及他的创作动机时,小子“二杆子”劲头上来了,两个眼珠子瞪得溜圆,磐石般的额头前倾,上下嘴巴黑森森的胡茬子冒着钢锭样的青光,厚厚的嘴唇显得性烈如火,那神态活活像一头要顶架的犍子牛,话出口竟“冒天下之大不韪”:毛泽东的名字和毛泽东思想一样,已不再是毛泽东躯体的符号,而是中国革命和在长期中国革命实践斗争经验的结晶。现在对毛泽东思想的说法,是讲毛泽东思想不能记在毛泽东个人的账上,而是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集体智慧之集大成。这是对的,而且是绝对正确。可是,现在一提毛泽东的错误,就不讲“集体主义”了,似乎都变成了“受害者”,千错万错都是毛泽东一个人的错,这符合实际么?远的不说,就拿“文革”讲,毛泽东是应该负主要责任,可是有主要不是还有个次要么?那么,那些个应该是次要角色的人士哪里去了?“四人帮”固然跑不了,可是除此还有没有呢?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确不再代表他本人,而是代表了一代甚至几代人。这样,要是彻底否定毛泽东,不就是要彻底否定一代甚至几代人么?这也不符合中央精神。现在社会上那些要操毛泽东娘的家伙本身自己的娘就被操了!因为他过去要末就标榜是毛泽东的忠诚拥护者,要末就宣称是毛泽东思想的忠实信徒。我就是毛泽东思想的忠实信徒,而且比基督徒信奉耶稣还虔诚。不然,我拼命往共产党里挤干什么?还不是觉得毛泽东伟大,对毛泽东思想崇拜?!
不久,呈“洛阳纸贵”现象的在全国大小书店和书摊上铺天盖地摆放着《走下神坛的毛泽东》一书,并赫然印着“权延赤著”几个颇有些“好汉做事好汉当”气势的黑体字。当然,我也几乎在同时以责任编辑的名义出版了他的另一部著作《掌上千秋——陕北时期的毛泽东和江青》,征订数也十分可观。一时间,全国形成上下争相说“神坛”。
“神坛”一书的问世,就像书名一样,毛泽东从“神”变成了人,变成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变成了一个既有领袖风范和经天纬地的雄才大略的伟人,又是一个有七情六欲和儿女情长的人,给人以“平地起高峰,高峰依平地”之感受。权延赤在“神坛”里既没有粉饰毛泽东,也没有丑化毛泽东,表现了一个作家的诚实和责任。当然,权延赤这种“顶风上”的结果,无疑会招致不少麻烦。那种压力,非一般人所能承受。如果不是小子骨头硬,非“趴架”不可。可是权延赤却至今硬是站立着,并且站立得愈发从容,愈发潇洒。
如今,权延赤已经像我一样“解甲归田”,并且比我“归田”得还彻底。他不是转业是复员,由一名师级干部变成一个地道的“小小老百姓”。不过,他活得并不卑贱,并不低下,反而较之一些“扛牌牌”的还富有,还充实,还硬气。权延赤的复员,熔铸着一种硬汉的不畏“权”,不惧“势”,不怕“穷”的气质和傲骨。
权延赤硬汉的气派,平时表现最锋芒毕露的是在喝酒上。他虽非嗜酒如命的酒徒,但他因斗勇贪杯却是实际。他喝酒从不服输,无论是年轻力壮、时还是如今已逾知天命之年,只要有人提出与他干杯,他就是明知道将酩酊大醉也从不装熊服输,而是抢先端起酒杯一扬脖子来个杯底朝天,并还将酒杯亮给对方加以证实。所以,经常有他喝醉后在楼道里睡到天亮的传闻,也有他喝醉后在女同胞面前“失态”的“花边”新闻,也有他一连四十天常醉常喝的辉煌。就在前不久,他因冠心病住院,医生严肃告诉他已经是酒精中毒如果再贪杯非出危险不可。可是,当有个朋友请他吃饭,两个人酒过三巡又对酒干杯,一共喝了五瓶“干白”外加两瓶半斤装的二锅头。事后他说,只要拿起酒杯时,就觉得我的酒量是“老子天下第一”,再加上谁要说我是怕死不敢喝,我听了觉得比骂我是“狗娘养的”还难受!当然,这种在酒杯上的“硬”,既损身,又误事,而且还有损“形象”,不是作为褒奖加以渲染,但为了写一个真实的权延赤是不得不据实道来的。
二
写下《硬汉权延赤》,一些读者来信来电希望我换一个角度谈谈权延赤。明明知道权延赤不好谈,恰恰反映权延赤气质的事情又不便谈,也只得应下。既然前一篇是从“硬件”上说的,那么本文就说点“软性”的吧。
讲权延赤是“多情汉子”,是说他喜欢交朋友。无论是文坛上的朋友还是军界、政界、商界的朋友以及“三教九流”的朋友乃至“酒肉朋友”他都交,并且交起来山呼海啸,有声有色,有滋有味。当然这些朋友中又分男女,可他从不“偏食”,一视同仁,以诚相待,“投之以桃,报之以李”。
权延赤的朋友,一部分属于职业圈内的范围。诸如报社、杂志社、出版社的朋友,大多是因作品交往而结交。还有,搞创作,断不了深入生活或写点报告文学之类的作品,那就需采访被写作的对象和知情者,谈两次熟悉了自然也就成为朋友了。可是,在权延赤的朋友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在饭桌上先认识的。权延赤端起酒杯那副轰轰烈烈不喝个海枯池干不服输的样子,那话出口越是“隐私”越敢往外端的坦诚,那天王老子也敢评头论足的无畏,一顿饭下来,原来拘谨的陌生面孔便变成称兄道弟的“哥儿们”了。
“为朋友两肋插刀”,在权延赤身上就不是一句套话,而是实实在在的行动。他掏腰包资助过多少朋友,当朋友“遇事”他跑过多少趟公安局或者“走过”多少关系,暂且不提,单讲他为朋友的“需要”代笔发表的作品,少说也有几十万字,足可以“造就”出几个小有名气的作家。搞文学创作的大多是惜墨如金,把发表作品看得跟儿子一样金贵。有的作家把名利看得高于一切,两人合作因谁的名字该署在前谁的名字该署在后而吵得天翻地覆,唾沫星子水龙头似的往对方脸上飞,王八蛋驴日的骂得狗血淋头。甚至有的还对簿公堂,一方恨不得叫另一方蹲几年大牢。我原来所在的创作单位,就有这类货色。可是权延赤为朋友,一篇一篇的作品拱手相送,一不要名,二不要利,活脱脱一个“义务劳动者”。
“要交朋友,就要讲情义,不然不成畜牲了!”这就是权延赤对交朋友的“座右铭”。
当然,在权延赤交的朋友中也出了一些“犹大”,可他认为这不奇怪;朋友多了会什么人都有,都变成“铁哥儿们”,反而倒是奇怪了。只要自己不坑朋友,就不会失眠,酒喝起来就照样是翻江倒海,山呼海啸。
讲权廷赤是“多情汉子”,是他的确有容易“动情”的一面。
权延赤在写作《红墙内外》时,采访毛泽东当年的卫士尹荆山。尹荆山言及在“三年困难”时期,毛泽东的小女儿李讷上大学,学校在北京郊区,距中南海很远,当时的交通又不方便。李讷只有星期天才回家。那年月,全国都饿,毛泽东给卫士们规定:第一,李讷从学校回中南海不许用汽车接;第二,叫李讷在学校食堂吃饭,不许去学校给她送饼干什么的。
那天,李讷从学校回到中南海,脸色蜡黄蜡黄的,一副有气无力的样子。卫士问她是不是病了,她说太饿了。卫士看着李讷说话时充满饥饿的目光,知道她一定饿得实在难熬了,就斗胆偷偷到毛泽东的小灶拿了几个玉米面与小麦面掺合在一起做成的金银卷。李讷接过来狼吞虎咽地吃下肚,还说饿。卫士见李讷饿成这个样子,眼圈红了。他们知道,站在面前的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金枝玉叶般的“公主”呀!她明明在学校吃不饱,又正值发育年龄,去学校给她送点饼干或者每天叫她回来跟主席一起吃顿饭又有什么过份呢?虽然主席每天也是粗茶淡饭,但总是可以吃饱呀。可是主席就是不许可。谁都知道毛泽东对他这个小女儿最疼爱,可是谁都又知道毛泽东对子女的管教也最严厉。卫士们常常记忆犹新的是毛泽东对其爱子毛岸英的严格要求。毛岸英刚从苏联回国,毛泽东就叫他到农村参加劳动;土改运动刚开始,毛泽东叫毛岸英到农村访贫问苦;抗美援朝战争爆发,毛泽东又叫毛岸英到硝烟滚滚的战场,最后献出了他年轻的生命!主席为革命死了多少亲人啊!卫士不忍心李讷再忍受饥饿的折磨,又跑到主席“小灶”拿了几块饼干叫李讷吃。结果被毛泽东看到了。他把卫士叫进屋,一拍桌子,大发雷霆,声色俱厉地质问:“三令五申,为什么还要搞特殊化?”卫士辩解:“李讷太饿了。再说,别的家长也有给孩子送吃的呀。”毛泽东听罢反而火气更大了:“别人可以送,我的孩子一块饼干也不许送!”这时李讷跑进来,抱着气得微微颤抖的毛泽东,给卫士求情地说:
“爸爸,是我喊饿,不怪叔叔们,是我太饿了呀!”毛泽东见到心爱的女儿,急忙俯下身去,一面抚摸着李讷的头,一面话音有些喑哑地安慰她说:“娃娃,我的好娃娃,乖娃娃,爸爸知道你饿,可是全国人民都在受饿呀!等全国人民都能吃饱了,爸爸再也不会叫你饿了。”当时在场的江青听到这里,作为李讷的母亲,不知是对毛泽东的“无情”表示不满,还是忍受不了这种场面的刺激,一扬下颏儿,急忙回房间去了。此刻的毛泽东,也抑制不住感情地冲出几步走到院子里。
卫士见状,马上跟出去,禁不住继续向毛泽东说:“主席,李讷正在长身体,是不是每天晚饭叫她回来吃,就一顿。”谁知毛泽东听罢,仰望长空,话出口如大江东去,一泻千里:“还是不行哟,谁叫她是我毛泽东的女儿哩!”……
尹荆山讲述到这里,突然觉得很静。惊讶地一看,访问他的权延赤用手死死捂着嘴巴,眼泪决堤似地汹涌。也已经动情的尹荆山问他怎么了,这时的权延赤再也控制不住了,接着发出了一个壮汉的嚎啕雷鸣。那大哭是对领袖风范“高山仰止”的赞颂,也是他充沛感情的酣畅宣泄。
“情”字,如果从字面上诠释,还有男女相爱之意。称得上一条烈性汉子的权延赤,体内也有二十二对染色体,荷尔蒙比一般人还发达。毋庸讳言,他无疑也会有七情六欲。但是,足以令权延赤自豪的是他有一个牢不可破的家庭,在这个牢不可破的家庭中,有他的爱人和他的爱女。笔者常听他爱人亲昵地使用“我们延赤……”那滴着甜蜜的字眼儿,这大概应该能说明不容易说清楚的“问题”的吧。
“多情汉子”权延赤,将会有更多的“未了情”。
三
最近因笔者写下《硬汉权延赤》和《多情汉子权延赤》两篇文章,接连收到不少读者来函,有的恳切要余转告权延赤少贪杯为宜,免得身心受损;有的言之凿凿要余牵线搭桥,与权延赤交个朋友;但更多的是尖锐地提出一个问题:既然权延赤那么热衷于交朋友,又时常喝得酩酊大醉,还有不少艳事绯闻,据了解他是个高产作家,如今他已“下海”,他哪还有工夫写那些大部头的著作?然而,无独有偶,与此仿佛殊途同归的是,传闻,卸下戎装后的权延赤时常去南方帮助朋友做点事儿,几乎整日价泡在酒缸里,为了偿还文债,特地聘了个“小秘”,待酒醒,他口述,“小秘”记录,稿成后,他粗粗修饰一番,便大功告成。还有的说得更邪乎,当权延赤文兴大发时,对着录音机神侃一通,然后高价请个“笔杆子”为他整理,最后他稍加润色,署上自己的大名,一部著作就这样抛出了笼。这些“嚼老婆舌头”的飞短流长说得有鼻子有眼儿,令人难置可否。
这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答案是什么呢?
先说前者。权延赤的确交友甚广,无须赘述。但这对于他来讲算作“平时”,即在他不想写作或者尚未进入写作状态时。不想写或写作的前期准备没有做充分而硬写,只能是挤牙膏,既慢又没有激情,也写不出好作品。作家的激情燃烧不起来写出来的东西能叫读者燃烧激情么?所以还不如干脆来个不写。既然不写东西总不能成天扎在书堆里,因此天性好交友的权延赤便与朋友来往频频,把盏杯杯,海阔天空,雅的俗的,荤的素的,胡侃一通。他认为,在与朋友的聊天中,时常有“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之感,并且好多作品的素材就是在聊天中得到的。因而,他觉得与朋友交往也不失为一种深入生活的形式。可是,一俟他写作激情难耐了,不动笔手都痒痒了,便找个偏僻地方“猫”起来,开始“奋笔疾书”。这时,他对自己采取的几乎是“全封闭”状态。他戏谑地称自己这个时期像做“白区”工作,上不告父母,下不告老婆孩子。有几次笔者有急事找他,他爱人告诉我“猫儿”到外边写东西去了。我问他躲到什么地方去了,他爱人说不知道。我和他爱人应该说比较熟,用权延赤的话说,她爱人对我的“感觉”还可以,所以就当面讲出我急于要找到他的因由,谁知他爱人听罢为难地说:“老权的脾气你不是不知道,我只知道他在什么方位,但不知道他具体在什么地点。”我进而逼问:“那万一家中有急事要找他呢?”他爱人答:“他时常给家里来电话,他从来不告诉他的电话号码。再说,就是我知道,我也不敢透露出去,不然,他回来保准得冲着我吼一顿。”事已如此,还怎么再难为他爱人呢?可见,权延赤写作时用军人式的手段强行排除一切干扰,切断与外界一切联系,全身心地投入到写作之中。用这种状态写作,能不高产么?权延赤告诉笔者,他运用这种“猫儿术”,采取的是“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开始离北京越远越好,慢慢朝北京游弋,最后就是“猫”在北京,也无妨了。
再说后者。对于他请“小秘”代劳的传闻是否属实?身在京都的余本无发言权。但凑巧的是,不久前为找权延赤索稿得以到南方“飞”了一趟。交谈时,我郑重地给他提起这个问题,问传闻到底是真是假。他听了两条浓眉鞭梢般飞起,眼瞪似豹,冲口滚出一声雷:“胡扯!”接着告诉我,他在南方与朋友交往属交往,但只要进入写作阶段,便闭门谢客,要是有朋友到宾馆找他,楼下大厅的值班经理先给他挡驾,要是实在挡不住驾,也要先用电话给他联系,待他同意后才允许客人到他居住的房间。他说你信不信,你要不信,我带你下楼你装扮一个找我的客人亲身体验一下。可见权延赤即使在南方要写东西还是能静下心来,“猫儿术”法力不减。
我听罢立刻作答:我马上说你讲的千真万确,你不觉得廉价么?我要是说你一派胡诌八咧,你小子眼珠子肯定瞪得牛卵子般大!我说信或者不信都无关紧要,你不历来都是“天马行空”么?
权延赤听完急忙大手巴掌一摆:“不,不不,对朋友的话我历来还是看重的。”
我噗哧一笑:“还叫我说什么呢,你交给我的这部洋洋20多万字的出自你手迹的大作,不就是最好的说明么?”
四
前几日与权延赤小聚,当他喝得“一塌糊涂”时,便“酒后吐真言”,滔滔话语澎湃汹涌。我挂一漏万地择其两件小事儿,品味再三,敷衍成文。
一次,权延赤的一位在京都也算个有头有脸儿的人物盛邀其捧场。可是不说“捧场”说“帮忙”。“帮什么忙?”权延赤逢事好问个究竟。“你老兄海量,打遍天下无敌手,当然是来个一醉方休了。”对方开口相告,但话语里却暗藏机关。权延赤明白,时下正如人说:“党政军民都经商,齐抓共管奔小康。”此话虽然有失偏颇,但在某种程度上又绝非无稽之谈。买卖人的谋略和手段在酒杯里,这话却不假。权延赤这次“帮忙”,可以说是喝了个天昏地暗,数数酒瓶子就有几十个。常言说没有不散的筵席,最后那个有头有脸儿的人物绅士派头地向服务小姐一打手势:“买单!”待服务员小姐款款地拿着菜单说出的钱数在他听来是个“天文”数字时,一时惊了个嘴大眼小,舌头像冻住似地打不过弯来。不知是他在这种场合自己从来没掏过腰包还是他的确囊中羞涩,要过菜单从头读到尾又从尾读到头。“小姐,你把菜单放错了地方,应该由我买单,给!”权延赤说着把一个可以付款的信用卡塞到服务员小姐手里。
这件事述说到这里无须再交待下文了,权延赤的大方可见一斑。当然,在权延赤与朋友的交往中像这样的例子可为鲜见,但他在与朋友交往中不惜慷慨解囊的事例委实是一抓一把。
权延赤坦言告之:“我喝醉了的时候是最大方,可是,我不醉的时候也很小气。”接着,便来个择实为据。
权延赤住在位于北京崇文区龙潭湖畔一个被称为“红楼”的部队住宅区,院落不大,楼房也已经破旧。在院门口两厢,时常有卖蔬菜的小摊小贩出没。这天,权延赤下楼买菜,见一个菜摊上菠菜很新鲜,问明价格后说:“买一斤。”当小贩给他秤好分量后,他以犀利的目光盯着小贩,问一句:“你给的分量够不够?”小贩闻听一梗脖子:“瞧你这人说的,我们做买卖的是卖不起不卖,绝不能缺斤少两。你要不信,去找个公平秤秤一秤,缺一补十,我说话算数。”“好,你既然这么说,那我们就讨个明白。”已经发觉这个小贩在分量上做了手脚的权延赤到附近的公平秤一称,一斤菠菜缺了一两。权延赤脸一镇,两条浓眉似利剑出鞘,话出口如滚过一声闷雷:“你说的,缺一补十,这斤菠菜我就白吃了,再见!”说完拔腿就走。
小贩一见急了,紧撵几步,一把抓住他的袖子:“想白吃我的菜,没那么容易!”权延赤返身驻足,厉声质问:“你不是说缺一补十吗?”小贩狡黠地一眨眼:“对,是我说过缺一补十,可是刚才我的眼睛一走神,看错了秤,我没说过敢保不看错秤呀?”血性汉子权延赤听完小贩的抵赖,好像人格受到莫大的污辱,脸涨得通红,一声怒吼似雄狮咆哮:“一些中国人所以卑贱猥琐,永远难成气候,就是你们这些小农经济者的产物!我没想过白吃这斤菠菜,可是看到你这副无赖似的嘴脸,这斤菠菜我是白吃定了。你放开手!”小贩受到权延赤的训斥,还要搭上一斤菠菜,气急败坏地跑到附近卖肉的摊位上抄起一把锋利的尖刀,满嘴喷着唾沫星子:“今天你不把菠菜给我放下,我就他妈地捅了你!”一时间,杀机骤起,空气立刻变得令人不寒而栗。可是,权延赤对小贩的持刀威吓非但没有畏惧,反而淡淡一笑:“来吧,你要是不怕蹲大狱,你就照着这儿捅!”他说罢放下菠菜,一挺胸脯,摆出一副视死如归的大丈夫气概。小贩本想吓唬权延赤一下,没想到居然遇上了这么一个威武不屈的汉子,立刻胆怯地一面往后退一面讨饶地说:“好好,今天算我倒霉,菠菜钱我不要了,你拿去白吃还不行嘛!”
“为一斤菠菜,值不了个块儿八角的,差点闹出一件人命案,你说我小气不小气?”权延赤讲完似问似答的说了一句,然后“嘿嘿”一笑,那笑容显得很天真,又很实在。
我说:“这怎么能算小气呢,说明你把‘人’字没有写歪,人的尊严没有趴下。你要是叫‘人’字再一抬胳臂,又慷慨一番,不就又成‘大’字了嘛。”
权延赤听了“嘿嘿”一乐,不知是赞赏我心有灵犀,还是笑我“够哥们儿”,属“爱乌及屋”。
写于1996年秋冬时节
我一听兀自犯难。因为越是朋友,越是交往频繁的朋友,越容易对彼此的言行举止“熟视无睹”,这就是往往出现的“墙内开花墙外香”的现象。还有,既然是老朋友,那么所披露的内容应该是鲜为人知的,对对方“质”的认识应该更冷僻,更独到,更深刻。不然,只择些许皮毛琐事,定会有辱“老友”称谓之崇高。
但是,为了刊物的“大局”需要,也就顾不得这许多了。于是,身为刊物主编的我便来个“恭敬不如从命”。
一
说权延赤是条硬汉子,倒不是指他身高一米八十开外的高大身躯和富有血性的殷红脸膛,也不是形容他那两道浓眉和声如狮吼的宏亮嗓音,而是说在长年的接触中,他首先给我“硬”的感觉,是他作为一名空军专业作家敢“硬”碰“硬”的创作。
“部队的作家写部队”,“空军的作家写空军”。这是部队主管文化艺术的部门几乎每年都要重申的口号。这个口号既是对部队专业作家的要求,又是检验作为一个部队专业作家的“硬性”尺度。虽然这个口号绝对没错,否则,“要是部队这么多作家都不写部队,那部队养这么多作家干什么”?谁又能说这句既是提问又是答案的话在逻辑上有什么谬误呢?既然作家是靠“养”,不报“养育”之恩岂不大逆不道?但是具体到创作上,几乎大多数作家都感到这个口号有点像孙猴子头上的“紧箍咒”,提起写部队题材就觉得头痛。因为对战争年代金戈铁马的生活该写的几乎都写过了,再写也难以写出新意,那么就只有在当代部队生活的田野里笔耕了。文艺的功能是“寓教于乐”。乐者,喜也,悦也,即兴致盎然之意。于文学作品,就是要设法让读者想看,爱看,以至达到“手不释卷”的程度,方为佳作。可是,和平建设期的部队生活,一没有刀光剑影,殊死搏杀,横扫千军;二没有运筹帷幄,指点江山,决胜千里;第三,反映部队生活题材的作品又要力避花前月下,缠缠绵绵,卿卿我我;特别是空军应该主要表现被誉为“天之骄子”的飞行员生活,可飞行员的真正舞台是驾驶歼击机在万米高空风驰电掣,作家本身一个个都是“旱鸭子”,怎么能对飞行员在空中的生活有切身的感受呢?没有感受到的东西却洋洋洒洒写成作品让读者去感受,不是地道的“挂羊头卖狗肉”么?还有一个极难言喻的原因,即部队是“柱石”,“柱石”是不能披露“斜度”和“阴影”的。所以,“要写又不好写”,“不写又不行”,因此大多数“聪明”的作家在两难之中有的搞“迂回战术”,有的巧用“嫁接技术”,有的索性来个“点缀法”,只要对付过去就行了。
然而,权延赤却不然。他从基层部队调到机关当专业作家,先是沉默了几年。据说是一连几个“猛子”扎到航空兵部队,待“厚积而薄发”。果然,权延赤不久便在部队“大哥大”刊物《解放军文艺》上发表出以“开天人”为系列的反映航空兵部队生活的中短篇小说,如春雷乍响,在沉寂的部队文坛激起巨大的波澜。接着,他又在河南人民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相继出版了反映空军生活的长篇小说《蔚蓝色的脚印》和《多欲之年》,可谓硕果累累。他那“硬”碰“硬”的“硬”劲儿,委实令“同好”还是原本就“不怎么好”的“笔杆子”们刮目相看了。当然,“同好”者多是钦佩与祝贺,“不怎么好”者则多是嫉妒与不屑了。
权延赤在创作生活中再一个敢于碰“硬”,则是有目共睹,抑或有口皆碑了。大凡诚实的人而不是文过饰非之辈都不会否认,权延赤在挥笔撰写《走下神坛的毛泽东》这部具有时代价值的纪实文学作品时,毛泽东的名字被当成咒骂和嘲弄的字眼儿为一些道貌岸然者和一些所谓屡经“浩劫”者所唾弃,那时的景况似乎谁诅咒毛泽东越耸人听闻越刻骨铭心谁就越伟大,越正确,越光彩。那时,我刚“解甲归田”转业到中国华侨出版公司不久,到权延赤家去约稿,得知他正奋笔疾书创作反映毛泽东生活的纪实性作品。当言及他的创作动机时,小子“二杆子”劲头上来了,两个眼珠子瞪得溜圆,磐石般的额头前倾,上下嘴巴黑森森的胡茬子冒着钢锭样的青光,厚厚的嘴唇显得性烈如火,那神态活活像一头要顶架的犍子牛,话出口竟“冒天下之大不韪”:毛泽东的名字和毛泽东思想一样,已不再是毛泽东躯体的符号,而是中国革命和在长期中国革命实践斗争经验的结晶。现在对毛泽东思想的说法,是讲毛泽东思想不能记在毛泽东个人的账上,而是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集体智慧之集大成。这是对的,而且是绝对正确。可是,现在一提毛泽东的错误,就不讲“集体主义”了,似乎都变成了“受害者”,千错万错都是毛泽东一个人的错,这符合实际么?远的不说,就拿“文革”讲,毛泽东是应该负主要责任,可是有主要不是还有个次要么?那么,那些个应该是次要角色的人士哪里去了?“四人帮”固然跑不了,可是除此还有没有呢?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确不再代表他本人,而是代表了一代甚至几代人。这样,要是彻底否定毛泽东,不就是要彻底否定一代甚至几代人么?这也不符合中央精神。现在社会上那些要操毛泽东娘的家伙本身自己的娘就被操了!因为他过去要末就标榜是毛泽东的忠诚拥护者,要末就宣称是毛泽东思想的忠实信徒。我就是毛泽东思想的忠实信徒,而且比基督徒信奉耶稣还虔诚。不然,我拼命往共产党里挤干什么?还不是觉得毛泽东伟大,对毛泽东思想崇拜?!
不久,呈“洛阳纸贵”现象的在全国大小书店和书摊上铺天盖地摆放着《走下神坛的毛泽东》一书,并赫然印着“权延赤著”几个颇有些“好汉做事好汉当”气势的黑体字。当然,我也几乎在同时以责任编辑的名义出版了他的另一部著作《掌上千秋——陕北时期的毛泽东和江青》,征订数也十分可观。一时间,全国形成上下争相说“神坛”。
“神坛”一书的问世,就像书名一样,毛泽东从“神”变成了人,变成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变成了一个既有领袖风范和经天纬地的雄才大略的伟人,又是一个有七情六欲和儿女情长的人,给人以“平地起高峰,高峰依平地”之感受。权延赤在“神坛”里既没有粉饰毛泽东,也没有丑化毛泽东,表现了一个作家的诚实和责任。当然,权延赤这种“顶风上”的结果,无疑会招致不少麻烦。那种压力,非一般人所能承受。如果不是小子骨头硬,非“趴架”不可。可是权延赤却至今硬是站立着,并且站立得愈发从容,愈发潇洒。
如今,权延赤已经像我一样“解甲归田”,并且比我“归田”得还彻底。他不是转业是复员,由一名师级干部变成一个地道的“小小老百姓”。不过,他活得并不卑贱,并不低下,反而较之一些“扛牌牌”的还富有,还充实,还硬气。权延赤的复员,熔铸着一种硬汉的不畏“权”,不惧“势”,不怕“穷”的气质和傲骨。
权延赤硬汉的气派,平时表现最锋芒毕露的是在喝酒上。他虽非嗜酒如命的酒徒,但他因斗勇贪杯却是实际。他喝酒从不服输,无论是年轻力壮、时还是如今已逾知天命之年,只要有人提出与他干杯,他就是明知道将酩酊大醉也从不装熊服输,而是抢先端起酒杯一扬脖子来个杯底朝天,并还将酒杯亮给对方加以证实。所以,经常有他喝醉后在楼道里睡到天亮的传闻,也有他喝醉后在女同胞面前“失态”的“花边”新闻,也有他一连四十天常醉常喝的辉煌。就在前不久,他因冠心病住院,医生严肃告诉他已经是酒精中毒如果再贪杯非出危险不可。可是,当有个朋友请他吃饭,两个人酒过三巡又对酒干杯,一共喝了五瓶“干白”外加两瓶半斤装的二锅头。事后他说,只要拿起酒杯时,就觉得我的酒量是“老子天下第一”,再加上谁要说我是怕死不敢喝,我听了觉得比骂我是“狗娘养的”还难受!当然,这种在酒杯上的“硬”,既损身,又误事,而且还有损“形象”,不是作为褒奖加以渲染,但为了写一个真实的权延赤是不得不据实道来的。
二
写下《硬汉权延赤》,一些读者来信来电希望我换一个角度谈谈权延赤。明明知道权延赤不好谈,恰恰反映权延赤气质的事情又不便谈,也只得应下。既然前一篇是从“硬件”上说的,那么本文就说点“软性”的吧。
讲权延赤是“多情汉子”,是说他喜欢交朋友。无论是文坛上的朋友还是军界、政界、商界的朋友以及“三教九流”的朋友乃至“酒肉朋友”他都交,并且交起来山呼海啸,有声有色,有滋有味。当然这些朋友中又分男女,可他从不“偏食”,一视同仁,以诚相待,“投之以桃,报之以李”。
权延赤的朋友,一部分属于职业圈内的范围。诸如报社、杂志社、出版社的朋友,大多是因作品交往而结交。还有,搞创作,断不了深入生活或写点报告文学之类的作品,那就需采访被写作的对象和知情者,谈两次熟悉了自然也就成为朋友了。可是,在权延赤的朋友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在饭桌上先认识的。权延赤端起酒杯那副轰轰烈烈不喝个海枯池干不服输的样子,那话出口越是“隐私”越敢往外端的坦诚,那天王老子也敢评头论足的无畏,一顿饭下来,原来拘谨的陌生面孔便变成称兄道弟的“哥儿们”了。
“为朋友两肋插刀”,在权延赤身上就不是一句套话,而是实实在在的行动。他掏腰包资助过多少朋友,当朋友“遇事”他跑过多少趟公安局或者“走过”多少关系,暂且不提,单讲他为朋友的“需要”代笔发表的作品,少说也有几十万字,足可以“造就”出几个小有名气的作家。搞文学创作的大多是惜墨如金,把发表作品看得跟儿子一样金贵。有的作家把名利看得高于一切,两人合作因谁的名字该署在前谁的名字该署在后而吵得天翻地覆,唾沫星子水龙头似的往对方脸上飞,王八蛋驴日的骂得狗血淋头。甚至有的还对簿公堂,一方恨不得叫另一方蹲几年大牢。我原来所在的创作单位,就有这类货色。可是权延赤为朋友,一篇一篇的作品拱手相送,一不要名,二不要利,活脱脱一个“义务劳动者”。
“要交朋友,就要讲情义,不然不成畜牲了!”这就是权延赤对交朋友的“座右铭”。
当然,在权延赤交的朋友中也出了一些“犹大”,可他认为这不奇怪;朋友多了会什么人都有,都变成“铁哥儿们”,反而倒是奇怪了。只要自己不坑朋友,就不会失眠,酒喝起来就照样是翻江倒海,山呼海啸。
讲权廷赤是“多情汉子”,是他的确有容易“动情”的一面。
权延赤在写作《红墙内外》时,采访毛泽东当年的卫士尹荆山。尹荆山言及在“三年困难”时期,毛泽东的小女儿李讷上大学,学校在北京郊区,距中南海很远,当时的交通又不方便。李讷只有星期天才回家。那年月,全国都饿,毛泽东给卫士们规定:第一,李讷从学校回中南海不许用汽车接;第二,叫李讷在学校食堂吃饭,不许去学校给她送饼干什么的。
那天,李讷从学校回到中南海,脸色蜡黄蜡黄的,一副有气无力的样子。卫士问她是不是病了,她说太饿了。卫士看着李讷说话时充满饥饿的目光,知道她一定饿得实在难熬了,就斗胆偷偷到毛泽东的小灶拿了几个玉米面与小麦面掺合在一起做成的金银卷。李讷接过来狼吞虎咽地吃下肚,还说饿。卫士见李讷饿成这个样子,眼圈红了。他们知道,站在面前的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金枝玉叶般的“公主”呀!她明明在学校吃不饱,又正值发育年龄,去学校给她送点饼干或者每天叫她回来跟主席一起吃顿饭又有什么过份呢?虽然主席每天也是粗茶淡饭,但总是可以吃饱呀。可是主席就是不许可。谁都知道毛泽东对他这个小女儿最疼爱,可是谁都又知道毛泽东对子女的管教也最严厉。卫士们常常记忆犹新的是毛泽东对其爱子毛岸英的严格要求。毛岸英刚从苏联回国,毛泽东就叫他到农村参加劳动;土改运动刚开始,毛泽东叫毛岸英到农村访贫问苦;抗美援朝战争爆发,毛泽东又叫毛岸英到硝烟滚滚的战场,最后献出了他年轻的生命!主席为革命死了多少亲人啊!卫士不忍心李讷再忍受饥饿的折磨,又跑到主席“小灶”拿了几块饼干叫李讷吃。结果被毛泽东看到了。他把卫士叫进屋,一拍桌子,大发雷霆,声色俱厉地质问:“三令五申,为什么还要搞特殊化?”卫士辩解:“李讷太饿了。再说,别的家长也有给孩子送吃的呀。”毛泽东听罢反而火气更大了:“别人可以送,我的孩子一块饼干也不许送!”这时李讷跑进来,抱着气得微微颤抖的毛泽东,给卫士求情地说:
“爸爸,是我喊饿,不怪叔叔们,是我太饿了呀!”毛泽东见到心爱的女儿,急忙俯下身去,一面抚摸着李讷的头,一面话音有些喑哑地安慰她说:“娃娃,我的好娃娃,乖娃娃,爸爸知道你饿,可是全国人民都在受饿呀!等全国人民都能吃饱了,爸爸再也不会叫你饿了。”当时在场的江青听到这里,作为李讷的母亲,不知是对毛泽东的“无情”表示不满,还是忍受不了这种场面的刺激,一扬下颏儿,急忙回房间去了。此刻的毛泽东,也抑制不住感情地冲出几步走到院子里。
卫士见状,马上跟出去,禁不住继续向毛泽东说:“主席,李讷正在长身体,是不是每天晚饭叫她回来吃,就一顿。”谁知毛泽东听罢,仰望长空,话出口如大江东去,一泻千里:“还是不行哟,谁叫她是我毛泽东的女儿哩!”……
尹荆山讲述到这里,突然觉得很静。惊讶地一看,访问他的权延赤用手死死捂着嘴巴,眼泪决堤似地汹涌。也已经动情的尹荆山问他怎么了,这时的权延赤再也控制不住了,接着发出了一个壮汉的嚎啕雷鸣。那大哭是对领袖风范“高山仰止”的赞颂,也是他充沛感情的酣畅宣泄。
“情”字,如果从字面上诠释,还有男女相爱之意。称得上一条烈性汉子的权延赤,体内也有二十二对染色体,荷尔蒙比一般人还发达。毋庸讳言,他无疑也会有七情六欲。但是,足以令权延赤自豪的是他有一个牢不可破的家庭,在这个牢不可破的家庭中,有他的爱人和他的爱女。笔者常听他爱人亲昵地使用“我们延赤……”那滴着甜蜜的字眼儿,这大概应该能说明不容易说清楚的“问题”的吧。
“多情汉子”权延赤,将会有更多的“未了情”。
三
最近因笔者写下《硬汉权延赤》和《多情汉子权延赤》两篇文章,接连收到不少读者来函,有的恳切要余转告权延赤少贪杯为宜,免得身心受损;有的言之凿凿要余牵线搭桥,与权延赤交个朋友;但更多的是尖锐地提出一个问题:既然权延赤那么热衷于交朋友,又时常喝得酩酊大醉,还有不少艳事绯闻,据了解他是个高产作家,如今他已“下海”,他哪还有工夫写那些大部头的著作?然而,无独有偶,与此仿佛殊途同归的是,传闻,卸下戎装后的权延赤时常去南方帮助朋友做点事儿,几乎整日价泡在酒缸里,为了偿还文债,特地聘了个“小秘”,待酒醒,他口述,“小秘”记录,稿成后,他粗粗修饰一番,便大功告成。还有的说得更邪乎,当权延赤文兴大发时,对着录音机神侃一通,然后高价请个“笔杆子”为他整理,最后他稍加润色,署上自己的大名,一部著作就这样抛出了笼。这些“嚼老婆舌头”的飞短流长说得有鼻子有眼儿,令人难置可否。
这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答案是什么呢?
先说前者。权延赤的确交友甚广,无须赘述。但这对于他来讲算作“平时”,即在他不想写作或者尚未进入写作状态时。不想写或写作的前期准备没有做充分而硬写,只能是挤牙膏,既慢又没有激情,也写不出好作品。作家的激情燃烧不起来写出来的东西能叫读者燃烧激情么?所以还不如干脆来个不写。既然不写东西总不能成天扎在书堆里,因此天性好交友的权延赤便与朋友来往频频,把盏杯杯,海阔天空,雅的俗的,荤的素的,胡侃一通。他认为,在与朋友的聊天中,时常有“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之感,并且好多作品的素材就是在聊天中得到的。因而,他觉得与朋友交往也不失为一种深入生活的形式。可是,一俟他写作激情难耐了,不动笔手都痒痒了,便找个偏僻地方“猫”起来,开始“奋笔疾书”。这时,他对自己采取的几乎是“全封闭”状态。他戏谑地称自己这个时期像做“白区”工作,上不告父母,下不告老婆孩子。有几次笔者有急事找他,他爱人告诉我“猫儿”到外边写东西去了。我问他躲到什么地方去了,他爱人说不知道。我和他爱人应该说比较熟,用权延赤的话说,她爱人对我的“感觉”还可以,所以就当面讲出我急于要找到他的因由,谁知他爱人听罢为难地说:“老权的脾气你不是不知道,我只知道他在什么方位,但不知道他具体在什么地点。”我进而逼问:“那万一家中有急事要找他呢?”他爱人答:“他时常给家里来电话,他从来不告诉他的电话号码。再说,就是我知道,我也不敢透露出去,不然,他回来保准得冲着我吼一顿。”事已如此,还怎么再难为他爱人呢?可见,权延赤写作时用军人式的手段强行排除一切干扰,切断与外界一切联系,全身心地投入到写作之中。用这种状态写作,能不高产么?权延赤告诉笔者,他运用这种“猫儿术”,采取的是“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开始离北京越远越好,慢慢朝北京游弋,最后就是“猫”在北京,也无妨了。
再说后者。对于他请“小秘”代劳的传闻是否属实?身在京都的余本无发言权。但凑巧的是,不久前为找权延赤索稿得以到南方“飞”了一趟。交谈时,我郑重地给他提起这个问题,问传闻到底是真是假。他听了两条浓眉鞭梢般飞起,眼瞪似豹,冲口滚出一声雷:“胡扯!”接着告诉我,他在南方与朋友交往属交往,但只要进入写作阶段,便闭门谢客,要是有朋友到宾馆找他,楼下大厅的值班经理先给他挡驾,要是实在挡不住驾,也要先用电话给他联系,待他同意后才允许客人到他居住的房间。他说你信不信,你要不信,我带你下楼你装扮一个找我的客人亲身体验一下。可见权延赤即使在南方要写东西还是能静下心来,“猫儿术”法力不减。
我听罢立刻作答:我马上说你讲的千真万确,你不觉得廉价么?我要是说你一派胡诌八咧,你小子眼珠子肯定瞪得牛卵子般大!我说信或者不信都无关紧要,你不历来都是“天马行空”么?
权延赤听完急忙大手巴掌一摆:“不,不不,对朋友的话我历来还是看重的。”
我噗哧一笑:“还叫我说什么呢,你交给我的这部洋洋20多万字的出自你手迹的大作,不就是最好的说明么?”
四
前几日与权延赤小聚,当他喝得“一塌糊涂”时,便“酒后吐真言”,滔滔话语澎湃汹涌。我挂一漏万地择其两件小事儿,品味再三,敷衍成文。
一次,权延赤的一位在京都也算个有头有脸儿的人物盛邀其捧场。可是不说“捧场”说“帮忙”。“帮什么忙?”权延赤逢事好问个究竟。“你老兄海量,打遍天下无敌手,当然是来个一醉方休了。”对方开口相告,但话语里却暗藏机关。权延赤明白,时下正如人说:“党政军民都经商,齐抓共管奔小康。”此话虽然有失偏颇,但在某种程度上又绝非无稽之谈。买卖人的谋略和手段在酒杯里,这话却不假。权延赤这次“帮忙”,可以说是喝了个天昏地暗,数数酒瓶子就有几十个。常言说没有不散的筵席,最后那个有头有脸儿的人物绅士派头地向服务小姐一打手势:“买单!”待服务员小姐款款地拿着菜单说出的钱数在他听来是个“天文”数字时,一时惊了个嘴大眼小,舌头像冻住似地打不过弯来。不知是他在这种场合自己从来没掏过腰包还是他的确囊中羞涩,要过菜单从头读到尾又从尾读到头。“小姐,你把菜单放错了地方,应该由我买单,给!”权延赤说着把一个可以付款的信用卡塞到服务员小姐手里。
这件事述说到这里无须再交待下文了,权延赤的大方可见一斑。当然,在权延赤与朋友的交往中像这样的例子可为鲜见,但他在与朋友交往中不惜慷慨解囊的事例委实是一抓一把。
权延赤坦言告之:“我喝醉了的时候是最大方,可是,我不醉的时候也很小气。”接着,便来个择实为据。
权延赤住在位于北京崇文区龙潭湖畔一个被称为“红楼”的部队住宅区,院落不大,楼房也已经破旧。在院门口两厢,时常有卖蔬菜的小摊小贩出没。这天,权延赤下楼买菜,见一个菜摊上菠菜很新鲜,问明价格后说:“买一斤。”当小贩给他秤好分量后,他以犀利的目光盯着小贩,问一句:“你给的分量够不够?”小贩闻听一梗脖子:“瞧你这人说的,我们做买卖的是卖不起不卖,绝不能缺斤少两。你要不信,去找个公平秤秤一秤,缺一补十,我说话算数。”“好,你既然这么说,那我们就讨个明白。”已经发觉这个小贩在分量上做了手脚的权延赤到附近的公平秤一称,一斤菠菜缺了一两。权延赤脸一镇,两条浓眉似利剑出鞘,话出口如滚过一声闷雷:“你说的,缺一补十,这斤菠菜我就白吃了,再见!”说完拔腿就走。
小贩一见急了,紧撵几步,一把抓住他的袖子:“想白吃我的菜,没那么容易!”权延赤返身驻足,厉声质问:“你不是说缺一补十吗?”小贩狡黠地一眨眼:“对,是我说过缺一补十,可是刚才我的眼睛一走神,看错了秤,我没说过敢保不看错秤呀?”血性汉子权延赤听完小贩的抵赖,好像人格受到莫大的污辱,脸涨得通红,一声怒吼似雄狮咆哮:“一些中国人所以卑贱猥琐,永远难成气候,就是你们这些小农经济者的产物!我没想过白吃这斤菠菜,可是看到你这副无赖似的嘴脸,这斤菠菜我是白吃定了。你放开手!”小贩受到权延赤的训斥,还要搭上一斤菠菜,气急败坏地跑到附近卖肉的摊位上抄起一把锋利的尖刀,满嘴喷着唾沫星子:“今天你不把菠菜给我放下,我就他妈地捅了你!”一时间,杀机骤起,空气立刻变得令人不寒而栗。可是,权延赤对小贩的持刀威吓非但没有畏惧,反而淡淡一笑:“来吧,你要是不怕蹲大狱,你就照着这儿捅!”他说罢放下菠菜,一挺胸脯,摆出一副视死如归的大丈夫气概。小贩本想吓唬权延赤一下,没想到居然遇上了这么一个威武不屈的汉子,立刻胆怯地一面往后退一面讨饶地说:“好好,今天算我倒霉,菠菜钱我不要了,你拿去白吃还不行嘛!”
“为一斤菠菜,值不了个块儿八角的,差点闹出一件人命案,你说我小气不小气?”权延赤讲完似问似答的说了一句,然后“嘿嘿”一笑,那笑容显得很天真,又很实在。
我说:“这怎么能算小气呢,说明你把‘人’字没有写歪,人的尊严没有趴下。你要是叫‘人’字再一抬胳臂,又慷慨一番,不就又成‘大’字了嘛。”
权延赤听了“嘿嘿”一乐,不知是赞赏我心有灵犀,还是笑我“够哥们儿”,属“爱乌及屋”。
写于1996年秋冬时节
看过本书的人还看过
-
文学小说 【已完结】
文君和韦晓晴成为情人时,并不知道马萍早已和别的男人好上了。其实马萍和别的男人好上这半年多的时间里,马萍从生理到心理是有一系列变化的,只因文君没有感觉到,如果在平时,文君是能感觉到的,因为文君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