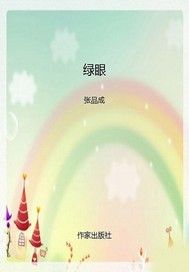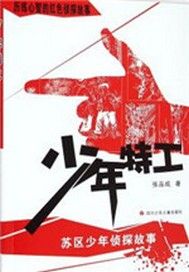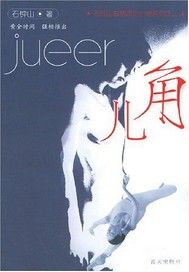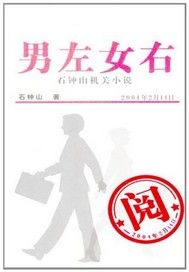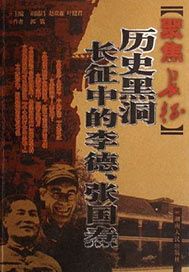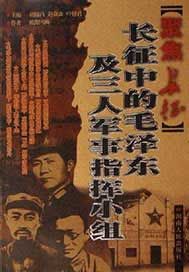当前位置:
文学小说
> 凌叔华:中国的曼殊斐儿
> 7
7
民国十七年(1930)秋天,凌福彭的身体江河日下。
李若兰给在美国的小女儿凌淑浩一连去信,详细描述了她父亲日趋恶化的健康状况。并说她父亲已回到南方,在那里,他能够从床边的窗户看见他的荔枝林。看了母亲的来信,凌淑浩本想回去看望父亲,但又不能拖着身子去做这样一次远渡重洋的长途旅行。托马斯·道远·陈(即淑浩儿子)出生后不久,她又接到一封家信,告知她父亲去世了,家人把他埋在番禺。
也是那一年,凌淑浩在美国匹茨堡完成医学实习后,接受了陈克恢(协和大学淑浩的老师)的求婚,于一九二九年七月十五日,在巴尔摩小教堂举行了婚礼。
仪式过后,凌淑浩坐上陈克恢的“双门纳什车”,在去印第安纳波利斯的途中度过四天蜜月,陈克恢便接受了伊利·李利制药公司为期一年(研制麻黄)的合同,凌淑浩做他研究室的助手。之后不久,凌淑浩发现自己怀孕了,她穿着一件大褂掩盖了七个月。
以此推算,凌淑浩生下儿子当是一九三○年的事了,而在《家国梦影》一书中魏淑凌写成“一九三三年秋”是不准确的。应该是婚后到一九三一年之前,她父亲从病重到病逝,她从怀孕到生子这段时间的事。
根据番禺深井村村志为凌志康提供的凌福彭的墓碑和材料所记,准确时间是一九三一年深秋。
凌福彭最早离开北京转道上海,又从上海回到广东城西荔枝湾,是在民国十六年(1927)春天,那时国民革命军北伐,占领了南京,时局很乱,上海(租界城市)成为比较安定的地方。受南方影响,北方的军阀政府也加紧思想控制,形势一天天恶化,加之学校常年欠薪,已不利于文化人的生存,因而许多学人纷纷南下上海谋职。胡适那时在美国访问,知此情况,干脆不回北京,直接去了上海。叶公超、梁实秋、刘英士、丁西林、饶孟侃等人,应暨南大学郑洪年校长之聘,也先后去了上海。
深井村村志提供的材料亦说,民国十六年(1927)凌福彭也去了上海,住在女儿凌淑萍家。因女儿与郑家结亲,凌福彭也与郑家父辈过从甚密,到上海后便与郑公馆比邻而居。
在上海住了一段时间后,外面传言,有人要绑架凌福彭,于是他便迅速离开上海,到广州荔枝湾“定香馆”二女儿凌雪山家居住。凌雪山的丈夫潘寿西是广州十三行富商潘文岩的后人,潘家原是福建同安人,乾隆间由闽到粤,入籍番禺。
导致凌福彭病逝的主要原因,是民国二十年(1931)秋天回乡祭祖。他不得不拖着病骨支离的身子,承担这次“主祭”之责,到深井后,是人们把他从车上抱下来的。这次祭祖,因路上受了风寒,回到广州他的病情便恶化了。
凌福彭病故后,在广州停棂“七期”,请僧人做道场,宾朋吊唁。深井村的材料说,他的棺椁是上等楠木做成,价值千两白银。到深井安葬,雇的是两只洞艇游乐船,一只运棺木,另一只运亲属,从珠江码头上船,沿江东下,再运到深井江沥海(村南边的河)码头下船,由杠夫抬往福旋冈墓地安葬。
凌福彭的墓碑是百天以后第二年壬申(1932)三月刻立的,碑文是:
清授光禄大夫润台府君
一品夫人先妣冯夫人墓
民国壬申三月祀子启恂、启凇孙念本、念赐、念曾、念珠立石
后来有乡人说凌福彭的墓地犯冲,“福旋者覆船也”。民国癸末(1943)孟冬,由叔华的兄长启恂、启淞迁墓地于大飞冈(坐寅向甲庚之原,向庚兼甲庚)。大飞冈在村北的飞鹅岭,珠江从脚下穿流而过,形如天鹅饮水,这里有深井八景之一“飞鹅饮涧”之称。
凌福彭的葬礼李若兰是否有偕女儿们参加,材料没有提及,查遍凌叔华的文字,没有一处写她父亲病逝的事,只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在小说《古韵》中写了早年对父亲的记忆。
而母亲李若兰用信件传递了凌福彭从生病到病逝的信息,成了家族中仅存的记忆,尽管时间上有些错位,细节应该是准确的。
呜乎!一代大儒凌福彭,就这样殒落了。
昙华林时代的凌叔华,接下来是否会走出生活的沉闷和寂寞呢?
李若兰给在美国的小女儿凌淑浩一连去信,详细描述了她父亲日趋恶化的健康状况。并说她父亲已回到南方,在那里,他能够从床边的窗户看见他的荔枝林。看了母亲的来信,凌淑浩本想回去看望父亲,但又不能拖着身子去做这样一次远渡重洋的长途旅行。托马斯·道远·陈(即淑浩儿子)出生后不久,她又接到一封家信,告知她父亲去世了,家人把他埋在番禺。
也是那一年,凌淑浩在美国匹茨堡完成医学实习后,接受了陈克恢(协和大学淑浩的老师)的求婚,于一九二九年七月十五日,在巴尔摩小教堂举行了婚礼。
仪式过后,凌淑浩坐上陈克恢的“双门纳什车”,在去印第安纳波利斯的途中度过四天蜜月,陈克恢便接受了伊利·李利制药公司为期一年(研制麻黄)的合同,凌淑浩做他研究室的助手。之后不久,凌淑浩发现自己怀孕了,她穿着一件大褂掩盖了七个月。
以此推算,凌淑浩生下儿子当是一九三○年的事了,而在《家国梦影》一书中魏淑凌写成“一九三三年秋”是不准确的。应该是婚后到一九三一年之前,她父亲从病重到病逝,她从怀孕到生子这段时间的事。
根据番禺深井村村志为凌志康提供的凌福彭的墓碑和材料所记,准确时间是一九三一年深秋。
凌福彭最早离开北京转道上海,又从上海回到广东城西荔枝湾,是在民国十六年(1927)春天,那时国民革命军北伐,占领了南京,时局很乱,上海(租界城市)成为比较安定的地方。受南方影响,北方的军阀政府也加紧思想控制,形势一天天恶化,加之学校常年欠薪,已不利于文化人的生存,因而许多学人纷纷南下上海谋职。胡适那时在美国访问,知此情况,干脆不回北京,直接去了上海。叶公超、梁实秋、刘英士、丁西林、饶孟侃等人,应暨南大学郑洪年校长之聘,也先后去了上海。
深井村村志提供的材料亦说,民国十六年(1927)凌福彭也去了上海,住在女儿凌淑萍家。因女儿与郑家结亲,凌福彭也与郑家父辈过从甚密,到上海后便与郑公馆比邻而居。
在上海住了一段时间后,外面传言,有人要绑架凌福彭,于是他便迅速离开上海,到广州荔枝湾“定香馆”二女儿凌雪山家居住。凌雪山的丈夫潘寿西是广州十三行富商潘文岩的后人,潘家原是福建同安人,乾隆间由闽到粤,入籍番禺。
导致凌福彭病逝的主要原因,是民国二十年(1931)秋天回乡祭祖。他不得不拖着病骨支离的身子,承担这次“主祭”之责,到深井后,是人们把他从车上抱下来的。这次祭祖,因路上受了风寒,回到广州他的病情便恶化了。
凌福彭病故后,在广州停棂“七期”,请僧人做道场,宾朋吊唁。深井村的材料说,他的棺椁是上等楠木做成,价值千两白银。到深井安葬,雇的是两只洞艇游乐船,一只运棺木,另一只运亲属,从珠江码头上船,沿江东下,再运到深井江沥海(村南边的河)码头下船,由杠夫抬往福旋冈墓地安葬。
凌福彭的墓碑是百天以后第二年壬申(1932)三月刻立的,碑文是:
清授光禄大夫润台府君
一品夫人先妣冯夫人墓
民国壬申三月祀子启恂、启凇孙念本、念赐、念曾、念珠立石
后来有乡人说凌福彭的墓地犯冲,“福旋者覆船也”。民国癸末(1943)孟冬,由叔华的兄长启恂、启淞迁墓地于大飞冈(坐寅向甲庚之原,向庚兼甲庚)。大飞冈在村北的飞鹅岭,珠江从脚下穿流而过,形如天鹅饮水,这里有深井八景之一“飞鹅饮涧”之称。
凌福彭的葬礼李若兰是否有偕女儿们参加,材料没有提及,查遍凌叔华的文字,没有一处写她父亲病逝的事,只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在小说《古韵》中写了早年对父亲的记忆。
而母亲李若兰用信件传递了凌福彭从生病到病逝的信息,成了家族中仅存的记忆,尽管时间上有些错位,细节应该是准确的。
呜乎!一代大儒凌福彭,就这样殒落了。
昙华林时代的凌叔华,接下来是否会走出生活的沉闷和寂寞呢?
看过本书的人还看过
-
文学小说 【已完结】
文君和韦晓晴成为情人时,并不知道马萍早已和别的男人好上了。其实马萍和别的男人好上这半年多的时间里,马萍从生理到心理是有一系列变化的,只因文君没有感觉到,如果在平时,文君是能感觉到的,因为文君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