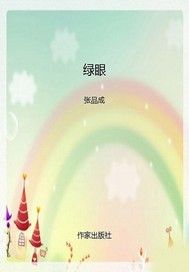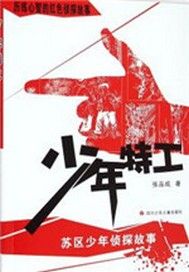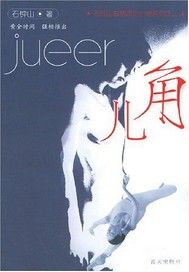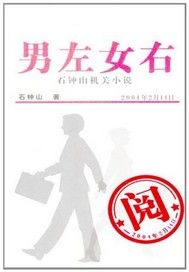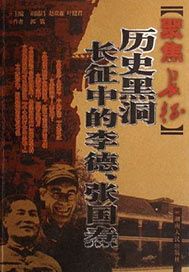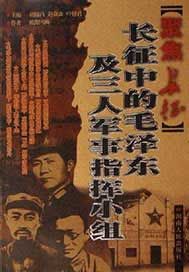第10章 宁静的小镇
2011年3月
一、梵高的终点
小镇是奥维,亦称奥维尔。位于巴黎北部的远郊,这一地理位置有点像家乡的慈城之于宁波城区的位置。慈城也是位于宁波的城北。
选择去奥维缘于梵高。印象派画家梵高在奥维走完了生命历程,而梵高的《向日葵》烙在我记忆里数十年。然而从巴黎去奥维要比从宁波去慈城远,且并不那么方便。从巴黎去奥维没有直达的公交线或长途专车,也没有旅游专线。尽管如此,我还是要去奥维看梵高。
巴黎的冬天比夏天醒得晚,比家乡的冬天亦醒得晚,时钟虽敲过七点,天地间仍是黑乎乎,路灯照亮了远远近近的街巷,而一杆灯光只像天上的星星忽明忽暗。不知是昨日询问的艰难,还是今晨赶路的匆忙,使得儿子一进车厢就发问:“巴黎有那么多的景区,还去奥维看疯子,是不是我们也疯了?”
“不要抬高自己了,你能割下耳朵当礼物送吗?”
就这么一问一答间,我们坐火车去奥维。
约莫坐了一个钟头,列车在瓦勒蒙特瓦站停靠。去奥维还要转车。法国的火车站建造得比较简单,有的没有专门的候车室,像家乡的公交站,简易的站台只建一个敞开的候车亭;有的站台上虽建房子,但这小房子承担了候车、售票、问讯、购物、告示、办公多种功能。瓦勒蒙特瓦站便是如此。两条铁轨伸向远方,窄长的站台上有间小屋。推门进去,空间有家居的客厅那般大,没有座椅,只设一广告栏,摆了一台自动销售柜,售票与问讯设在这间小屋的同一窗口,一女服务员坐在窗口值班。这种布局很像家乡萧甬线上的丈亭、叶家之类的小站,当年长龙似的绿皮火车曾经停靠于瓦站这样的站台边上。如今,在家乡,这样的小站早已废弃不用了,如常去的慈城的小站。不过,慈城站似乎比瓦勒蒙特瓦站还要大一些,至少有专门的候车室。
我们徘徊在空荡荡的站台上,不经意间发现小屋正面镶嵌了一块铜牌,是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铜牌。这块长不足一米的纪念牌上刻了两排法文,大意是一群男人于1939—1945年被纳粹分子残杀。尽管没有详细的介绍,我们还是驻足细看,法西斯的屠刀曾经在这里挥舞过,正义的鲜血曾经染红这一块土地……纪念牌似乎拉近了我们与这一陌生土地的距离。其实,我们仅仅停留十四分钟,不过是匆匆的旅行者,然而我记住了法兰西大地上的普通小站——瓦勒蒙特瓦站,那是巴黎与奥维间的一个驿站。开往奥维的车来了,我再回首看那小站,看那小屋,看那铜牌,家乡的慈城站也有类似抵抗罪恶屠刀的事件,但我们有这样的纪念牌吗?
又坐了十来分钟的车,抵达向往多年的奥维。
奥维站的大小与瓦勒蒙特瓦站相似,不同的是奥维站候车处开辟了一块展区,里面挂的是梵高的作品,熟悉的如《向日葵》《加谢大夫》《奥维教堂》《麦田群鸦》,不熟悉的有《花园里的玛格丽特》。
走出车站,是陌生的小镇,我们机械地沿着马路左拐向前走去,所见的民居都紧闭院门,紧闭窗户,两车道的马路上偶尔有车辆穿梭,我们听得到轮子与地面的摩擦声。小镇静悄悄的,奥维人似乎还在睡梦中。走着走着,我们发现,小镇的居民喜用水彩画作门牌。一百多年前的初夏,梵高听从弟弟提奥的建议来奥维找加谢医生治病。那么,水彩画作门牌是因梵高,还是古已有之的小镇民俗呢?小镇坐北朝南,地势南低北高。以火车站为基准,往西是加谢医生的家,往北是哈雾旅店,那是梵高的故居,往东北则是梵高画笔下的教堂,还有梵高开枪自杀的麦田……我们似乎还想了解没有梵高痕迹的奥维,便按图索骥走向城堡。
人处陌生之地,不由自主产生迷茫。其实城堡近在咫尺,我们还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幸好有一奥维人推着自行车穿过古城墙走来,儿子迎上前询问。我看她的车把上挂了一个布袋,两根长棍面包(baguette)的头露出袋口,想必她与家乡的大嫂一样正买早餐而归。城堡建于17世纪,如今里面展现的是19世纪末的巴黎和印象派发展的历史,不巧的是这天城堡不开放。“去杜比里博物馆,那儿有工作人员提供帮助……”这位法国女士建议道。
我们进城去杜比里博物馆。杜比里是梵高欣赏的画家,比梵高早几十年定居奥维。我们由北而南,步行五六分钟,有一花园映入眼帘,院内有一幢别墅,别墅正居中印有蓝色棱形作底的红色“i”标记,这是在异国他乡看到的较为亲切的标记,因为在有这种记号的地方,我们能得到所需的帮助。走上一楼,接待我们的是一位法国姑娘。我们希望找一位导游,她摇摇头,微笑着送给我们一张奥维导游图。导游图是份复印件,法国姑娘按我们口述的景点用黄绿色荧光笔作了大小不一的方块记号,然后用手指在图纸上“行走”了一遍。我环顾四周,这里除了介绍杜比里外,还陈列着有关梵高的纪念品:以梵高和他的作品为主题的明信片、光碟、画册,法文、英文、日文版的梵高传,还有世界各国的研究文章。末了法国姑娘又问我们还需要什么帮助,说这里有梵高的生平介绍,还有关于他的纪念品。
来之前,我们从网上搜索奥维,所有介绍小镇的资料几乎都与梵高相关。到了奥维才知,小镇与梵高联系得更加紧密,满目的梵高作品,遍地的梵高遗迹,似乎在告诉人们奥维为梵高而建,梵高又为奥维而生。而如此与名人紧密相联的小镇——奥维,却没有因梵高而喧哗。不是吗?在奥维,我们没有碰到摇着三角旗的旅游团队,虽然在梵高的墓前,我们曾看到向梵高献花的游客。
我们登上梵高画笔下的奥维教堂,俯视小镇,街上没有太多的行人,民居有的紧闭院门,有的敞开却不见人,屋顶的烟囱仍不见炊烟,小镇静得似一幅画……再往远眺望,我们看到了瓦涅河,河上行驶的船,亦是悄然无声,静得似一幅水墨画,这就是如画的奥维,一个宁静的小镇。
二、麦儿青青
可能是因雨的滋润,也可能是因雪的融化,通往麦田的小路有些泥泞,幸亏路口竖有一块牌子,牌子上是梵高的《麦田群鸦》,这样就免去了泥泞中的寻找。
是一百多年前的故事,是《麦田群鸦》,召唤我来这里;还是一百多年前的故事,还是《麦田群鸦》,让我感觉眼前的麦田与众不同。
麦儿青青。麦田的西面被树林包围,东面紧挨墓园,北端伸向远方,像火车轨道似的消失于天与地的衔接处。倘若没有梵高,倘若没有《麦田群鸦》,那只是平常的麦田。事实也是如此,麦田极其平常,与家乡的麦田没什么两样,麦儿极其平常,亦与家乡的麦儿没什么两样。倒是画面中的场景与眼前的景色不同。画中的麦儿已经成熟,麦浪金黄,有力地翻滚,一片乌云席卷而来,一群乌鸦盘旋于上空。而眼前的景色,天高云淡,叶片青青的麦儿刚刚钻出地面,一苗苗,一簇簇,与或荣或枯的草儿混杂一起,难辨哪是麦儿,哪是野草。是季节的差别,还是艺术的张力?不知奥维的麦子成熟期与家乡是否一样,也在夏天?如果是这样,那奥维的夏天,是否与家乡的夏天一样,午后时有雷阵雨?雷阵雨来临前夕,头顶是红黄色的火烧云,之后风驰云涌时,黑云盖过了火烧云。如果是这样,那是否是红黄色,或是黄色点燃梵高的激情,使他在红黄色的火烧云下,在黄色的麦田绝笔,一个壮年的生命被火烧云燃烧,被麦浪吞噬;从而使平常的麦田流传了不寻常的故事,使一个宁静的小镇让全世界瞩目。
1853年,梵高出生于奥维往北的一个荷兰牧师家庭。有六个兄弟姐妹相伴,排行老大的他度过了欢乐的童年。16岁时,梵高离家南下。在异国他乡,他做过画工,曾研究古画,以继承家业。还是为了继承家业,学过神学的梵高曾在一个矿区传教授课……梵高力求以男人的力量做事谋生。然命运不济,一次矿难事故中梵高救助了受伤的矿工,这样身体力行传授博爱,理应得到颂扬,不知为何,却被教会指责有失尊严。这是命运的摆布,还是触犯了人的尊卑之序?疑惑中,梵高放弃神圣职业改行绘画。
十九世纪的七八十年代,巴黎渐兴印象画流派。这一艺术流派用光和色彩表现画家捕捉的自然景色的瞬间印象,从而激荡了传统画坛。按理说,梵高的转行恰逢时机。梵高不太喜欢荷兰的郁金香,而是喜欢法国的向日葵。这种喜欢近乎狂热,他一次又一次画向日葵。一次,他画了黄色为基调的《向日葵》后,寄给提奥,并在附上的书信中写道:“我画的向日葵也值得那些苏格兰人或美国人出500法郎(时合100美元)。”然而,命运似乎和他开了个玩笑。梵高钟情的《向日葵》在他生前却无人问津。不仅如此,甚至还有画家不愿与“那盆不堪的向日葵”一同展出。这对一个以画求生的职业画家是多么大的打击哟!有意思的是,如今这幅《向日葵》与印象派的奠基之作——莫奈的《日出·印象》齐名。约百年后的1987年3月,这幅《向日葵》在伦敦拍卖得3985万美金。近40万倍的差距,这不是命运对梵高开的玩笑,又是什么呢?
也许,大师就是这么磨炼而成的?
梵高一生的油画作品有八百多幅,但不少是雷同的主题,他的《向日葵》也是如此。他曾画了十二幅亮黄的向日葵作为“新家”的装饰。这个“新家”在阿尔,是梵高租居的地方,后以“黄色小屋”著称。
阿尔位于法国南部普罗旺斯地区。只可惜我这次法国之行没时间去阿尔。阿尔是梵高炼狱人生的最后两站之一。梵高于1888年2月去阿尔。在那儿,他画向日葵,画水果成熟的果园,画辛勤的农夫……普罗旺斯的骄阳晒红了他的皮肤,晒焦了他的红发,同时似乎也是普罗旺斯的骄阳不断地刺激着梵高的创作热情,使他的艺术生涯达到鼎盛。根据梵高的年谱,他的主要作品差不多都诞生在他有生的最后两年。而最后的两年,他差不多就生活在阿尔与奥维。也是这最后两年,命运之于梵高已不再是开玩笑那样轻松,而是烈日下的煎熬般痛苦。因为在这最后的两年,这位渴望面包、渴望爱情的男人彻底地“疯狂”了。
严格地说,引起潜伏的精神疾病基因裂变的是梵高22岁时那次失恋。起初,梵高也只是间歇发病,只是轻微的精神错乱,人们不知他的病情。精神病患者大多自己不觉,梵高也是如此。他的家人不知,他的朋友不知,就连身为同胞手足的提奥也没有想到家族病会发生在苦难的哥哥身上。在凡人的世间,世俗的眼光中,无边无际想象的艺术家,多是另类的“疯子”。梵高的喜怒无常自然而然地被视作一个艺术家的个性。然而,阿尔的割耳事件,惊醒了同仁,惊醒了家人——梵高“疯”了。
那是梵高抵阿尔不久。画家高更也去阿尔。梵高为迎接朋友的到来,用十二幅向日葵装饰了家,用鲜亮的黄色颜料涂抹了一遍。高更抵达后,两人一起外出作画,一起回家切磋,但两人却志同而不和,时常吵架。一次吵架时,梵高无法控制自己。可能是为了避开发怒的梵高,高更离家外出。梵高见状,跟随而出,手里紧握一把画刀,据说想暗杀高更,不过没举刀又转身回了黄色小屋。面对黄色的向日葵,梵高激情燃烧,举起刀,“嚓”的一下,割下自己的耳朵,然后用报纸裹好血淋淋的耳朵,再次出门将它送给女友……梵高疯了,先被送进圣雷米精神病院,后来奥维。来奥维,是提奥的建议。提奥让梵高找加谢医生治病。加谢医生是个业余画家,弟弟希望在宁静的小镇,哥哥能与加谢心灵相通,有共同的语言。
1890年5月20日,梵高来到奥维。出火车站不远,离加谢医生家较近有家哈雾旅店。旅店不大,时价3.5法郎一天的住宿费还包一日三餐,囊中羞涩的梵高下榻哈雾旅店。
梵高找到加谢医生。梵高对医生的印象居然是“他病得比我还要严重”。不知真是如此,还是对绘画一样的痴情所致的错觉,加谢还是实现了提奥的心愿,这位“患病”的医生还真成了梵高的朋友。治病之余,加谢常邀请梵高来家里聚餐,聊天。梵高乐于此,也时常为加谢的家人画像。加谢喜爱梵高的画。一次要梵高的自画像,梵高没给,提笔替加谢画像,这样,又一幅名作——《加谢医生的肖像》诞生了。这幅画如今用在奥维导游图上。有意思的是,当年梵高绘画时,特将加谢的头发画成红黄色。这与梵高画向日葵时用的艺术手法相同。高更说,梵高作画用心。正如高更所言,梵高作画用的是心,而且用的是一颗像向日葵一样向着太阳的心。也许正是因为如此,梵高早将心灵相通的加谢认作自己的太阳了,因为梵高离开阿尔的精神病院来到奥维时,他的病情日益加剧。他在给提奥的信中说道:“我的生活,从根基上被破坏,我的脚只能跛着走。”然而“跛着走”的梵高,却在奥维创作了《有杉树的道路》《花园里的玛格丽特》《奥维的教堂》……一个精神完全或者说几近崩溃且身心孤独的病人还能够如此清醒地绘画,说明他肯定有一个知音及支持者,而加谢就是梵高生命中最后的知音抑或支持者,这一支持之于一个病人无疑是冬天的太阳那般的温暖。
精神病无情地折磨着梵高。麦田的麦子扬花抽穗,由青转黄。麦儿开始成熟,此时的梵高看到了“不安的天空下面大片延伸的麦田”,他想“把我在乡下见到的生机勃勃的景象告诉你”。梵高走进黄灿灿的麦田,面对麦浪翻滚,心神荡漾的他再一次提起画笔,提起刮刀,用一颗荡漾的心将不安的麦田、不安的群鸦定格在苍白的画布上——《麦田群鸦》诞生了。此后的梵高再也无法控制犹如麦浪般翻滚的心,终于在1890年7月27日,最后一次走进不安的天空下面大片延伸的麦田,这一次梵高拿的不是画笔,而是手枪。面对麦浪翻滚,心神荡漾的梵高拿起了手枪,将枪口对准了自己的胸膛,“砰”的一声,枪声惊起了群鸦……枪声,惊动了提奥。翌日,提奥来奥维。面对因枪伤痛苦不已的哥哥,兄弟俩聊起童年时光。童年的往事也许能缓解梵高的疼痛,却赶不走死神。一天后,梵高在哈雾旅店告别了他疯狂绘画的小镇、疯狂绘画的世界。
麦儿青青,站在《麦田群鸦》这份特殊的遗书前,我默默无言,不知该用什么方式去拜谒这位生前寂寞、身后辉煌的艺术大师。
三、梵高之幸
我们缓步走向墓园。
这是祖祖辈辈的奥维人将灵魂送上天国之后,留存躯体的地方。墓园不大,四周围了一道矮墙,西面的矮墙镶了两扇铁门。一大一小的铁门将阴阳隔开。梵高的坟茔就在北面的墙根。提奥的坟墓与他并排,在他的右侧,一样的大小,一样的墓碑。墓碑下方顶圆,深色的石碑刷了一层粉白色的涂料。石碑阴刻了兄弟俩的姓名,生卒年月,白底黑字,一目了然。没有多余的碑文,没有任何雕饰,如同生命的本真。
假如时光倒流一百多年,假如用世俗的眼光评价梵高,他生前绝对是个失败者。数百幅作品生前只卖掉一幅,要票子没有票子:他生活所需的票子是提奥给的,医疗上的票子是提奥给的,就连买画笔的票子也是提奥给的。要女人没女人:好不容易相中了女人,彼此也有点相爱,可不是遭遇女方父母的反对,就是自己没有钱留不住心仪的女人。想想也是,一个名利皆空的画家,连自己都靠弟弟接济,怎能养活妻儿呢?这样一个情爱缺失,只在世上活了37年,没有儿女的男人,怎能说成功呢?想必这是梵高的不幸。然而,不幸的梵高身后却十分幸运。那幸运是天无绝人之路。那就是这个生前病困交加、缺情少爱的男人居然遇到一个甘心为他做事的女人。
这个女人是提奥的妻子,他的弟媳乔安娜·邦格。因为性情所至,梵高的一生孤情缺爱寡欢。然而,生前身后,他却不缺兄弟之情。提奥是他生活上的靠山,是他艺术上的知音,人生难得一知己,这是梵高之幸。梵高开枪自残归天后,提奥无比哀伤,竟然也精神失常,不到半年,带着让全世界看到梵高的画的遗愿也撒手归天……
提奥的离世,乔安娜不胜哀伤。虽然乔安娜嫁到夫家不足一年半,屈指算来与梵高相处的时间只有五天。然而这位英文高才生、荷兰女人,深爱丈夫和他的家人,包括疯狂作画的梵高。每当孤独时,每当思念时,年仅29岁的提奥遗孀做的是同一件事,那就是阅读梵高写给提奥的书信。五百多封书信,数百次心灵对话。这样的阅读,让这个女人读出了两个男人的手足之情,读出了一个男人的非凡成就,也让她因爱这个男人而成为这个男人知音的知音。这个女人由此也明白了自己的担当。乔安娜的哥哥安德烈不喜欢油画,曾经劝妹妹丢掉这些废布。所幸乔安娜没有听从安德烈的话,否则人们将不知梵高是谁,人类将与一位艺术大师失之交臂。
让全世界看到梵高的画——提奥的遗愿也成为这个女人的人生目标。乔安娜开始张罗梵高的画展了,同时,利用自己的语言优势,夜以继日将梵高的书信译成英文,以等待画展成功时,配合出版梵高的信札。然而,推介这位被人们视为疯子的艺术家并非易事,而且此前梵高是一直被冷落的艺术家。事实也是如此,十年间举办的六次梵高画展,每次都是以观众漠然而告终。等到第七次再展梵高的作品时,人们才稍有心动,之后欧洲一些著名美术馆的大门才为这位天才加疯子的艺术家敞开。此时的乔安娜又伺机出售梵高的一些作品,一来换些钱贴补家用,一来提升梵高的名气。功夫不负有心人,乔安娜的努力终于使原本名不见经传的梵高作品有了市场。而此时的乔安娜,似乎完成自己的担当似的,离开人间去了天国。那一年,乔安娜63岁。这个女人为完成所爱男人的遗愿,为向世人展现她相知的男人的才华而足足努力了34年。如果梵高真能在天国遇到乔安娜的话,想必他一定会给这个女人画幅肖像。梵高一生中为不少人画了肖像,他们中有医生、农夫,他也画过自画像,唯独没有为家人画过肖像。这不能不说是个遗憾。
乔安娜离世后,梵高的作品全部由提奥与乔安娜的独子小文生继承。小文生没有继承伯父绘画的才华,也没有继承父母经营艺术的才能,这位学工程的男人独守着灿烂的艺术宝库多年。后来,当荷兰政府收购梵高的作品时,小文生以在阿姆斯特丹盖一座“国立梵高美术馆”等要求,出售梵高的所有作品,这样小文生也因贫穷的伯父而成荷兰的首富。
如果没有梵高,我们可能不会来奥维。如果不来奥维,我们可能也不会去解读梵高。如今,梵高和他弟弟并肩长眠地下,一片爬山虎叶像一块厚厚的毛毯覆盖在他们的身上。梵高墓旁有株不知名的小树,因为冬季,小树叶谢果落,到春来发几枝时,小树定是郁郁葱葱,树枝与墓碑左侧的那簇小红花一起摇曳,一年又一年,像为梵高的艺术而歌,而舞。
麦儿青青,墓园寂静,我伫立梵高坟茔前,注视着墓碑上的文字“VAN GOGH”,默默地向这位伟大的画家致敬!冯骥才先生说过,梵高的奇迹是天才加上精神病。想想也是,世间众多画家,有几个能像梵高那样疯狂地作画呢?梵高的一生历经了由肉体的折磨至思想的飞跃,由思想的飞跃至艺术的升华与涅槃。于梵高,饥饿、疾病可以说是命运的玩笑,同时也恰恰是对大师的磨砺。只有这样,梵高的作品才具备无与伦比的艺术光芒,而正是这种艺术光芒,为人类艺术宝库增添了巨大财富。梵高的奇迹,还在于生前的病困交加,身后大富大贵,这是人间的悲喜剧,或多或少带给我们深思。也许正因为此,我要来奥维,要来拜谒梵高,因为梵高是个画家,更是哲学家,他用他的作品,他的人生诠释幸与不幸的关系,而这又不是我等俗人说得清的!
一、梵高的终点
小镇是奥维,亦称奥维尔。位于巴黎北部的远郊,这一地理位置有点像家乡的慈城之于宁波城区的位置。慈城也是位于宁波的城北。
选择去奥维缘于梵高。印象派画家梵高在奥维走完了生命历程,而梵高的《向日葵》烙在我记忆里数十年。然而从巴黎去奥维要比从宁波去慈城远,且并不那么方便。从巴黎去奥维没有直达的公交线或长途专车,也没有旅游专线。尽管如此,我还是要去奥维看梵高。
巴黎的冬天比夏天醒得晚,比家乡的冬天亦醒得晚,时钟虽敲过七点,天地间仍是黑乎乎,路灯照亮了远远近近的街巷,而一杆灯光只像天上的星星忽明忽暗。不知是昨日询问的艰难,还是今晨赶路的匆忙,使得儿子一进车厢就发问:“巴黎有那么多的景区,还去奥维看疯子,是不是我们也疯了?”
“不要抬高自己了,你能割下耳朵当礼物送吗?”
就这么一问一答间,我们坐火车去奥维。
约莫坐了一个钟头,列车在瓦勒蒙特瓦站停靠。去奥维还要转车。法国的火车站建造得比较简单,有的没有专门的候车室,像家乡的公交站,简易的站台只建一个敞开的候车亭;有的站台上虽建房子,但这小房子承担了候车、售票、问讯、购物、告示、办公多种功能。瓦勒蒙特瓦站便是如此。两条铁轨伸向远方,窄长的站台上有间小屋。推门进去,空间有家居的客厅那般大,没有座椅,只设一广告栏,摆了一台自动销售柜,售票与问讯设在这间小屋的同一窗口,一女服务员坐在窗口值班。这种布局很像家乡萧甬线上的丈亭、叶家之类的小站,当年长龙似的绿皮火车曾经停靠于瓦站这样的站台边上。如今,在家乡,这样的小站早已废弃不用了,如常去的慈城的小站。不过,慈城站似乎比瓦勒蒙特瓦站还要大一些,至少有专门的候车室。
我们徘徊在空荡荡的站台上,不经意间发现小屋正面镶嵌了一块铜牌,是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铜牌。这块长不足一米的纪念牌上刻了两排法文,大意是一群男人于1939—1945年被纳粹分子残杀。尽管没有详细的介绍,我们还是驻足细看,法西斯的屠刀曾经在这里挥舞过,正义的鲜血曾经染红这一块土地……纪念牌似乎拉近了我们与这一陌生土地的距离。其实,我们仅仅停留十四分钟,不过是匆匆的旅行者,然而我记住了法兰西大地上的普通小站——瓦勒蒙特瓦站,那是巴黎与奥维间的一个驿站。开往奥维的车来了,我再回首看那小站,看那小屋,看那铜牌,家乡的慈城站也有类似抵抗罪恶屠刀的事件,但我们有这样的纪念牌吗?
又坐了十来分钟的车,抵达向往多年的奥维。
奥维站的大小与瓦勒蒙特瓦站相似,不同的是奥维站候车处开辟了一块展区,里面挂的是梵高的作品,熟悉的如《向日葵》《加谢大夫》《奥维教堂》《麦田群鸦》,不熟悉的有《花园里的玛格丽特》。
走出车站,是陌生的小镇,我们机械地沿着马路左拐向前走去,所见的民居都紧闭院门,紧闭窗户,两车道的马路上偶尔有车辆穿梭,我们听得到轮子与地面的摩擦声。小镇静悄悄的,奥维人似乎还在睡梦中。走着走着,我们发现,小镇的居民喜用水彩画作门牌。一百多年前的初夏,梵高听从弟弟提奥的建议来奥维找加谢医生治病。那么,水彩画作门牌是因梵高,还是古已有之的小镇民俗呢?小镇坐北朝南,地势南低北高。以火车站为基准,往西是加谢医生的家,往北是哈雾旅店,那是梵高的故居,往东北则是梵高画笔下的教堂,还有梵高开枪自杀的麦田……我们似乎还想了解没有梵高痕迹的奥维,便按图索骥走向城堡。
人处陌生之地,不由自主产生迷茫。其实城堡近在咫尺,我们还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幸好有一奥维人推着自行车穿过古城墙走来,儿子迎上前询问。我看她的车把上挂了一个布袋,两根长棍面包(baguette)的头露出袋口,想必她与家乡的大嫂一样正买早餐而归。城堡建于17世纪,如今里面展现的是19世纪末的巴黎和印象派发展的历史,不巧的是这天城堡不开放。“去杜比里博物馆,那儿有工作人员提供帮助……”这位法国女士建议道。
我们进城去杜比里博物馆。杜比里是梵高欣赏的画家,比梵高早几十年定居奥维。我们由北而南,步行五六分钟,有一花园映入眼帘,院内有一幢别墅,别墅正居中印有蓝色棱形作底的红色“i”标记,这是在异国他乡看到的较为亲切的标记,因为在有这种记号的地方,我们能得到所需的帮助。走上一楼,接待我们的是一位法国姑娘。我们希望找一位导游,她摇摇头,微笑着送给我们一张奥维导游图。导游图是份复印件,法国姑娘按我们口述的景点用黄绿色荧光笔作了大小不一的方块记号,然后用手指在图纸上“行走”了一遍。我环顾四周,这里除了介绍杜比里外,还陈列着有关梵高的纪念品:以梵高和他的作品为主题的明信片、光碟、画册,法文、英文、日文版的梵高传,还有世界各国的研究文章。末了法国姑娘又问我们还需要什么帮助,说这里有梵高的生平介绍,还有关于他的纪念品。
来之前,我们从网上搜索奥维,所有介绍小镇的资料几乎都与梵高相关。到了奥维才知,小镇与梵高联系得更加紧密,满目的梵高作品,遍地的梵高遗迹,似乎在告诉人们奥维为梵高而建,梵高又为奥维而生。而如此与名人紧密相联的小镇——奥维,却没有因梵高而喧哗。不是吗?在奥维,我们没有碰到摇着三角旗的旅游团队,虽然在梵高的墓前,我们曾看到向梵高献花的游客。
我们登上梵高画笔下的奥维教堂,俯视小镇,街上没有太多的行人,民居有的紧闭院门,有的敞开却不见人,屋顶的烟囱仍不见炊烟,小镇静得似一幅画……再往远眺望,我们看到了瓦涅河,河上行驶的船,亦是悄然无声,静得似一幅水墨画,这就是如画的奥维,一个宁静的小镇。
二、麦儿青青
可能是因雨的滋润,也可能是因雪的融化,通往麦田的小路有些泥泞,幸亏路口竖有一块牌子,牌子上是梵高的《麦田群鸦》,这样就免去了泥泞中的寻找。
是一百多年前的故事,是《麦田群鸦》,召唤我来这里;还是一百多年前的故事,还是《麦田群鸦》,让我感觉眼前的麦田与众不同。
麦儿青青。麦田的西面被树林包围,东面紧挨墓园,北端伸向远方,像火车轨道似的消失于天与地的衔接处。倘若没有梵高,倘若没有《麦田群鸦》,那只是平常的麦田。事实也是如此,麦田极其平常,与家乡的麦田没什么两样,麦儿极其平常,亦与家乡的麦儿没什么两样。倒是画面中的场景与眼前的景色不同。画中的麦儿已经成熟,麦浪金黄,有力地翻滚,一片乌云席卷而来,一群乌鸦盘旋于上空。而眼前的景色,天高云淡,叶片青青的麦儿刚刚钻出地面,一苗苗,一簇簇,与或荣或枯的草儿混杂一起,难辨哪是麦儿,哪是野草。是季节的差别,还是艺术的张力?不知奥维的麦子成熟期与家乡是否一样,也在夏天?如果是这样,那奥维的夏天,是否与家乡的夏天一样,午后时有雷阵雨?雷阵雨来临前夕,头顶是红黄色的火烧云,之后风驰云涌时,黑云盖过了火烧云。如果是这样,那是否是红黄色,或是黄色点燃梵高的激情,使他在红黄色的火烧云下,在黄色的麦田绝笔,一个壮年的生命被火烧云燃烧,被麦浪吞噬;从而使平常的麦田流传了不寻常的故事,使一个宁静的小镇让全世界瞩目。
1853年,梵高出生于奥维往北的一个荷兰牧师家庭。有六个兄弟姐妹相伴,排行老大的他度过了欢乐的童年。16岁时,梵高离家南下。在异国他乡,他做过画工,曾研究古画,以继承家业。还是为了继承家业,学过神学的梵高曾在一个矿区传教授课……梵高力求以男人的力量做事谋生。然命运不济,一次矿难事故中梵高救助了受伤的矿工,这样身体力行传授博爱,理应得到颂扬,不知为何,却被教会指责有失尊严。这是命运的摆布,还是触犯了人的尊卑之序?疑惑中,梵高放弃神圣职业改行绘画。
十九世纪的七八十年代,巴黎渐兴印象画流派。这一艺术流派用光和色彩表现画家捕捉的自然景色的瞬间印象,从而激荡了传统画坛。按理说,梵高的转行恰逢时机。梵高不太喜欢荷兰的郁金香,而是喜欢法国的向日葵。这种喜欢近乎狂热,他一次又一次画向日葵。一次,他画了黄色为基调的《向日葵》后,寄给提奥,并在附上的书信中写道:“我画的向日葵也值得那些苏格兰人或美国人出500法郎(时合100美元)。”然而,命运似乎和他开了个玩笑。梵高钟情的《向日葵》在他生前却无人问津。不仅如此,甚至还有画家不愿与“那盆不堪的向日葵”一同展出。这对一个以画求生的职业画家是多么大的打击哟!有意思的是,如今这幅《向日葵》与印象派的奠基之作——莫奈的《日出·印象》齐名。约百年后的1987年3月,这幅《向日葵》在伦敦拍卖得3985万美金。近40万倍的差距,这不是命运对梵高开的玩笑,又是什么呢?
也许,大师就是这么磨炼而成的?
梵高一生的油画作品有八百多幅,但不少是雷同的主题,他的《向日葵》也是如此。他曾画了十二幅亮黄的向日葵作为“新家”的装饰。这个“新家”在阿尔,是梵高租居的地方,后以“黄色小屋”著称。
阿尔位于法国南部普罗旺斯地区。只可惜我这次法国之行没时间去阿尔。阿尔是梵高炼狱人生的最后两站之一。梵高于1888年2月去阿尔。在那儿,他画向日葵,画水果成熟的果园,画辛勤的农夫……普罗旺斯的骄阳晒红了他的皮肤,晒焦了他的红发,同时似乎也是普罗旺斯的骄阳不断地刺激着梵高的创作热情,使他的艺术生涯达到鼎盛。根据梵高的年谱,他的主要作品差不多都诞生在他有生的最后两年。而最后的两年,他差不多就生活在阿尔与奥维。也是这最后两年,命运之于梵高已不再是开玩笑那样轻松,而是烈日下的煎熬般痛苦。因为在这最后的两年,这位渴望面包、渴望爱情的男人彻底地“疯狂”了。
严格地说,引起潜伏的精神疾病基因裂变的是梵高22岁时那次失恋。起初,梵高也只是间歇发病,只是轻微的精神错乱,人们不知他的病情。精神病患者大多自己不觉,梵高也是如此。他的家人不知,他的朋友不知,就连身为同胞手足的提奥也没有想到家族病会发生在苦难的哥哥身上。在凡人的世间,世俗的眼光中,无边无际想象的艺术家,多是另类的“疯子”。梵高的喜怒无常自然而然地被视作一个艺术家的个性。然而,阿尔的割耳事件,惊醒了同仁,惊醒了家人——梵高“疯”了。
那是梵高抵阿尔不久。画家高更也去阿尔。梵高为迎接朋友的到来,用十二幅向日葵装饰了家,用鲜亮的黄色颜料涂抹了一遍。高更抵达后,两人一起外出作画,一起回家切磋,但两人却志同而不和,时常吵架。一次吵架时,梵高无法控制自己。可能是为了避开发怒的梵高,高更离家外出。梵高见状,跟随而出,手里紧握一把画刀,据说想暗杀高更,不过没举刀又转身回了黄色小屋。面对黄色的向日葵,梵高激情燃烧,举起刀,“嚓”的一下,割下自己的耳朵,然后用报纸裹好血淋淋的耳朵,再次出门将它送给女友……梵高疯了,先被送进圣雷米精神病院,后来奥维。来奥维,是提奥的建议。提奥让梵高找加谢医生治病。加谢医生是个业余画家,弟弟希望在宁静的小镇,哥哥能与加谢心灵相通,有共同的语言。
1890年5月20日,梵高来到奥维。出火车站不远,离加谢医生家较近有家哈雾旅店。旅店不大,时价3.5法郎一天的住宿费还包一日三餐,囊中羞涩的梵高下榻哈雾旅店。
梵高找到加谢医生。梵高对医生的印象居然是“他病得比我还要严重”。不知真是如此,还是对绘画一样的痴情所致的错觉,加谢还是实现了提奥的心愿,这位“患病”的医生还真成了梵高的朋友。治病之余,加谢常邀请梵高来家里聚餐,聊天。梵高乐于此,也时常为加谢的家人画像。加谢喜爱梵高的画。一次要梵高的自画像,梵高没给,提笔替加谢画像,这样,又一幅名作——《加谢医生的肖像》诞生了。这幅画如今用在奥维导游图上。有意思的是,当年梵高绘画时,特将加谢的头发画成红黄色。这与梵高画向日葵时用的艺术手法相同。高更说,梵高作画用心。正如高更所言,梵高作画用的是心,而且用的是一颗像向日葵一样向着太阳的心。也许正是因为如此,梵高早将心灵相通的加谢认作自己的太阳了,因为梵高离开阿尔的精神病院来到奥维时,他的病情日益加剧。他在给提奥的信中说道:“我的生活,从根基上被破坏,我的脚只能跛着走。”然而“跛着走”的梵高,却在奥维创作了《有杉树的道路》《花园里的玛格丽特》《奥维的教堂》……一个精神完全或者说几近崩溃且身心孤独的病人还能够如此清醒地绘画,说明他肯定有一个知音及支持者,而加谢就是梵高生命中最后的知音抑或支持者,这一支持之于一个病人无疑是冬天的太阳那般的温暖。
精神病无情地折磨着梵高。麦田的麦子扬花抽穗,由青转黄。麦儿开始成熟,此时的梵高看到了“不安的天空下面大片延伸的麦田”,他想“把我在乡下见到的生机勃勃的景象告诉你”。梵高走进黄灿灿的麦田,面对麦浪翻滚,心神荡漾的他再一次提起画笔,提起刮刀,用一颗荡漾的心将不安的麦田、不安的群鸦定格在苍白的画布上——《麦田群鸦》诞生了。此后的梵高再也无法控制犹如麦浪般翻滚的心,终于在1890年7月27日,最后一次走进不安的天空下面大片延伸的麦田,这一次梵高拿的不是画笔,而是手枪。面对麦浪翻滚,心神荡漾的梵高拿起了手枪,将枪口对准了自己的胸膛,“砰”的一声,枪声惊起了群鸦……枪声,惊动了提奥。翌日,提奥来奥维。面对因枪伤痛苦不已的哥哥,兄弟俩聊起童年时光。童年的往事也许能缓解梵高的疼痛,却赶不走死神。一天后,梵高在哈雾旅店告别了他疯狂绘画的小镇、疯狂绘画的世界。
麦儿青青,站在《麦田群鸦》这份特殊的遗书前,我默默无言,不知该用什么方式去拜谒这位生前寂寞、身后辉煌的艺术大师。
三、梵高之幸
我们缓步走向墓园。
这是祖祖辈辈的奥维人将灵魂送上天国之后,留存躯体的地方。墓园不大,四周围了一道矮墙,西面的矮墙镶了两扇铁门。一大一小的铁门将阴阳隔开。梵高的坟茔就在北面的墙根。提奥的坟墓与他并排,在他的右侧,一样的大小,一样的墓碑。墓碑下方顶圆,深色的石碑刷了一层粉白色的涂料。石碑阴刻了兄弟俩的姓名,生卒年月,白底黑字,一目了然。没有多余的碑文,没有任何雕饰,如同生命的本真。
假如时光倒流一百多年,假如用世俗的眼光评价梵高,他生前绝对是个失败者。数百幅作品生前只卖掉一幅,要票子没有票子:他生活所需的票子是提奥给的,医疗上的票子是提奥给的,就连买画笔的票子也是提奥给的。要女人没女人:好不容易相中了女人,彼此也有点相爱,可不是遭遇女方父母的反对,就是自己没有钱留不住心仪的女人。想想也是,一个名利皆空的画家,连自己都靠弟弟接济,怎能养活妻儿呢?这样一个情爱缺失,只在世上活了37年,没有儿女的男人,怎能说成功呢?想必这是梵高的不幸。然而,不幸的梵高身后却十分幸运。那幸运是天无绝人之路。那就是这个生前病困交加、缺情少爱的男人居然遇到一个甘心为他做事的女人。
这个女人是提奥的妻子,他的弟媳乔安娜·邦格。因为性情所至,梵高的一生孤情缺爱寡欢。然而,生前身后,他却不缺兄弟之情。提奥是他生活上的靠山,是他艺术上的知音,人生难得一知己,这是梵高之幸。梵高开枪自残归天后,提奥无比哀伤,竟然也精神失常,不到半年,带着让全世界看到梵高的画的遗愿也撒手归天……
提奥的离世,乔安娜不胜哀伤。虽然乔安娜嫁到夫家不足一年半,屈指算来与梵高相处的时间只有五天。然而这位英文高才生、荷兰女人,深爱丈夫和他的家人,包括疯狂作画的梵高。每当孤独时,每当思念时,年仅29岁的提奥遗孀做的是同一件事,那就是阅读梵高写给提奥的书信。五百多封书信,数百次心灵对话。这样的阅读,让这个女人读出了两个男人的手足之情,读出了一个男人的非凡成就,也让她因爱这个男人而成为这个男人知音的知音。这个女人由此也明白了自己的担当。乔安娜的哥哥安德烈不喜欢油画,曾经劝妹妹丢掉这些废布。所幸乔安娜没有听从安德烈的话,否则人们将不知梵高是谁,人类将与一位艺术大师失之交臂。
让全世界看到梵高的画——提奥的遗愿也成为这个女人的人生目标。乔安娜开始张罗梵高的画展了,同时,利用自己的语言优势,夜以继日将梵高的书信译成英文,以等待画展成功时,配合出版梵高的信札。然而,推介这位被人们视为疯子的艺术家并非易事,而且此前梵高是一直被冷落的艺术家。事实也是如此,十年间举办的六次梵高画展,每次都是以观众漠然而告终。等到第七次再展梵高的作品时,人们才稍有心动,之后欧洲一些著名美术馆的大门才为这位天才加疯子的艺术家敞开。此时的乔安娜又伺机出售梵高的一些作品,一来换些钱贴补家用,一来提升梵高的名气。功夫不负有心人,乔安娜的努力终于使原本名不见经传的梵高作品有了市场。而此时的乔安娜,似乎完成自己的担当似的,离开人间去了天国。那一年,乔安娜63岁。这个女人为完成所爱男人的遗愿,为向世人展现她相知的男人的才华而足足努力了34年。如果梵高真能在天国遇到乔安娜的话,想必他一定会给这个女人画幅肖像。梵高一生中为不少人画了肖像,他们中有医生、农夫,他也画过自画像,唯独没有为家人画过肖像。这不能不说是个遗憾。
乔安娜离世后,梵高的作品全部由提奥与乔安娜的独子小文生继承。小文生没有继承伯父绘画的才华,也没有继承父母经营艺术的才能,这位学工程的男人独守着灿烂的艺术宝库多年。后来,当荷兰政府收购梵高的作品时,小文生以在阿姆斯特丹盖一座“国立梵高美术馆”等要求,出售梵高的所有作品,这样小文生也因贫穷的伯父而成荷兰的首富。
如果没有梵高,我们可能不会来奥维。如果不来奥维,我们可能也不会去解读梵高。如今,梵高和他弟弟并肩长眠地下,一片爬山虎叶像一块厚厚的毛毯覆盖在他们的身上。梵高墓旁有株不知名的小树,因为冬季,小树叶谢果落,到春来发几枝时,小树定是郁郁葱葱,树枝与墓碑左侧的那簇小红花一起摇曳,一年又一年,像为梵高的艺术而歌,而舞。
麦儿青青,墓园寂静,我伫立梵高坟茔前,注视着墓碑上的文字“VAN GOGH”,默默地向这位伟大的画家致敬!冯骥才先生说过,梵高的奇迹是天才加上精神病。想想也是,世间众多画家,有几个能像梵高那样疯狂地作画呢?梵高的一生历经了由肉体的折磨至思想的飞跃,由思想的飞跃至艺术的升华与涅槃。于梵高,饥饿、疾病可以说是命运的玩笑,同时也恰恰是对大师的磨砺。只有这样,梵高的作品才具备无与伦比的艺术光芒,而正是这种艺术光芒,为人类艺术宝库增添了巨大财富。梵高的奇迹,还在于生前的病困交加,身后大富大贵,这是人间的悲喜剧,或多或少带给我们深思。也许正因为此,我要来奥维,要来拜谒梵高,因为梵高是个画家,更是哲学家,他用他的作品,他的人生诠释幸与不幸的关系,而这又不是我等俗人说得清的!
看过本书的人还看过
-
文学小说 【已完结】
文君和韦晓晴成为情人时,并不知道马萍早已和别的男人好上了。其实马萍和别的男人好上这半年多的时间里,马萍从生理到心理是有一系列变化的,只因文君没有感觉到,如果在平时,文君是能感觉到的,因为文君不是...